作者简介
陈拓,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3年3期,注释从略。
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与中国人合作编译了大量汉文西学文献。虽然受礼仪之争、清廷禁教等影响,西学东渐在清中叶遭遇顿挫,但一些知识与文本最终跨越时空,转化为19世纪中国人认识新世界、应对新变局、接引新西学的“本土”资源。而明末清初反西学文献,同样成为19世纪中国人反西方科技(西技)、反基督宗教(西教)的文本与思想资源。对于前者,学界关注渐多,后者则鲜有探讨。由于传教士是清代传播西技的主力,故西技与西教常难以切割。为研究方便,本文将反西技与反西教概称为中性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泛指强调中国本位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一种倾向。
《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是明末清初反西学文献的代表:前两书编于明崇祯年间,作者多有佛教背景,主要反西教;而《不得已》(又称《不得已录》)由清初杨光先(1597—1669)所著,既反西教,又反西技,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康熙三年(1664)至八年,杨光先曾掀起“康熙历狱”,该书收录其反对西方历算学与天主教的论疏等。书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破邪集》《辟邪集》在明亡后,《不得已》在康熙后,均不同程度被淡忘。19世纪,《破邪集》《辟邪集》在日本的知名度远高于中国,安政二年(1855)、文久元年(1861)两书先后翻刻于日本,后又经日本重新输入中国。相较之下,《不得已》自嘉庆四年(1799)被黄丕烈、钱大昕等朴学家再发现后,犹如盘旋在国人思想中的一个“幽灵”,屡掀波澜。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所言:中国存在一种反基督宗教的传统,“它对19世纪中国士人的反教态度,不仅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成为其资源”,杨光先在西方威胁问题上“所传下来的紧迫感及他所提出的激烈方案,强有力地吸引着后来的中国人,对他们而言,西方入侵已成为首要现实问题”。柯文的观察虽极具启发性,但他主要立足于《不得已》与晚清反教文献在思维上的相似性,即抽象继承。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文学界从版本学切入,探究了《不得已》在后世的流传与影响。黄一农对《不得已》的版本做了大量开创性研究,其后陈占山、周岩、肖清和等续有深化。但他们侧重历狱与书籍本身,对其后世流传仅附带讨论,因此除序跋、传记等与版本直接相关的文献外,他们对更丰富的阅读史资料相对忽视,更未能动态地审视19世纪中国人对《不得已》的认识分歧与嬗变。
本文拟从阅读史切入,聚焦于《不得已》与19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间的思想互动,关注17世纪的杨光先如何“死而复活”,参与19世纪的思想进程。《不得已》阅读史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缩影。康熙历狱作为“中西争竞之大关键”,在明清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历算学的西胜中败,对康熙帝及中国士人触动颇大,他们致力于复兴中法,并倡导“西学中源”。杨光先作为失败者,逐渐淡出士人视野;嘉庆年间,因黄丕烈偶然购得《不得已》而引发一股阅读风,钱大昕、阮元、李锐、许宗彦等朴学家纷纷卷入,凌廷堪与孙星衍为此还展开了一场辩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局势变化,无论地方士人(苏州、常州等),还是上层官员(倭仁、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等),《不得已》均曾现身其阅读世界或话语场域中。《不得已》除直接流传外,还借助魏源《海国图志》间接流传,“开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竟成为极端排外的《辟邪纪实》的思想源头之一,甚至日本、朝鲜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是经由《海国图志》而接触到《不得已》。
一、朴学家与嘉庆初年《不得已》的再发现
晚明士人虽不乏排斥西学者,但主要着眼于宗教、政治与文化层面,而较少对西技进行学理批评。其原因正如钱大昕所言:“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中国士人长期重道轻器,明中后期儒者多不懂历算学,中国历算学自身的薄弱使其根本无力应对西方历算学的挑战。故徐光启坦陈:中国历算学不如西方历算学,西法“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他主张“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首先应大规模翻译西书。
随着西学的输入与实学的兴盛,晚明个别士人虽已开始致力于发掘、钻研中国传统历算学,但因明朝灭亡而未成气候。阮元明确称:“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入清后,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等一批中国本土历算学家逐渐成长起来。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虽由多重因素所促成,却是中西历算学当着皇帝、百官及天下人,以钦天监为舞台的一场面对面竞赛。凌廷堪犀利地指出:“此我朝中西争竞之大关键。”
历狱的发动者杨光先是徽州歙县人,顺治末年曾作《摘谬论》等具呈礼部,罗列耶稣会士汤若望所制西法历书的“十谬”,但未引起重视。康熙三年,他复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状》,并再次进呈《摘谬论》《选择议》,批评汤若望制历谬误、误择葬期等,引发康熙历狱,汤若望、南怀仁等被监禁。康熙四年,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他废除西法改用中法,在监副吴明炫协助下,于康熙七年主持编制了《民历》与《七政历》,但南怀仁批评该历置闰、节气等均误。已亲政的康熙帝下令召集南怀仁等传教士和杨光先、吴明炫等进行辩论,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康熙帝采纳南怀仁建议,命双方赴观象台测验正午时刻的日影长度,以实测这一无可置疑的方式,宣布西胜中败。
中法的落败,极大地刺激了康熙帝与中国士人。康熙帝在对皇子的庭训中追忆道:“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按:当为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在皇权的推动下,通过借鉴西法以及深入发掘、整理中国传统历算文献,中法开始渐能应对西法挑战,中西进入一个学术“争竞”期,历算学的地位也因争竞而显著提高。同时,康熙帝还屡次强调西法源出中法,于是“西学中源”逐渐占据官方及学界的主流话语。
清中叶朴学兴盛,历算学融为朴学的一部分,朴学家们纷纷涉足历算学,并将历算学应用于经史考订与义理发微。钱大昕甚至宣称:“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这既是中国经学的内在发展脉络使然,也是中西争竞的历史产物。失败者杨光先渐被淡忘,《不得已》在历狱结束后很快成为罕见之书。例如将杨光先视为乡贤的程廷祚,曾欲“求《不得已》之书,则渺不可得。闻此书初出,西人购以重赀,每部购以二百金,燔毁略尽”。西人购毁说后被戴震、钱大昕等发扬光大。学界多将此说视为谣传,虽然“二百金”显系夸张,但传教士委实曾购买回收一些对天主教不利的书籍。例如以常熟为传教中心的鲁日满,在1674年11月的账本中记载:“我花钱回收了三本对人有害的书籍:0.060两。”1675年1月又记载:“我以利类思神父的名义,给反对杨光先的书的印刷者:0.400两。”所回收的三书,鲁日满虽未罗列书名,但从他组织刊印反对杨光先的《崇正必辩》看,传教士的确在各地致力于消除杨光先的影响。西人购毁《不得已》虽很可能是事实,却非该书“渺不可得”的主因,杨光先在政治与科技上的双重失败才是关键。一百多年后,沉寂的《不得已》被朴学家们再次“发现”。
朴学家凌廷堪为杨光先歙县同乡,长期客居扬州。他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来“尤留心推步之学”,曾赴江宁寻访梅文鼎后人。嘉庆二年(1797),他致信阮元,强调康熙历狱是“中西争竞之大关键”,建议阮元搜寻《不得已》并查访事件始末:“此事官私之书皆不详,不及此时觅其《不得已书》并访诸耆旧,附见颠末,则愈久而愈湮没矣。”虽无下文,但可视为嘉庆初年《不得已》阅读风的肇端。
天缘凑巧,嘉庆四年,苏州藏书家黄丕烈竟偶然购得《不得已》!当时有“书估携此册求售”,黄丕烈“奇其名,故以白金一锭购之”。他最初对该书并未措意,后来其苏州同乡、数学家李锐告诉他,钱大昕“尝以未见此书为言”,方知为“罕觏之本”,于是加以装订,并邀钱大昕题跋。自乾隆五十四年受聘至嘉庆九年去世,钱大昕执掌苏州紫阳书院教习凡十六年。李锐曾跟随钱大昕学习历算学,知晓其师欲得《不得已》之心,故一直留意该书。钱大昕获见《不得已》后非常激动,他在跋中称:“向闻吾友戴东原说,欧罗巴人以重价购此书,即焚毁之,欲灭其迹也。今始于吴门黄氏学耕堂见之。”则他是从戴震处听闻该书。戴震虽在《四库全书》馆工作,但也未尝寓目《不得已》。钱大昕跋对杨光先持一分为二态度,否定其科学水准,而肯定其反天主教,他称:“杨君于步算非专家,又无有力助之者,故终为彼所诎。然其诋耶稣异教,禁人传习,不可谓无功于名教者矣。”其《竹汀先生日记钞》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杨光先“虽于推步非专门,其驳耶稣异教,禁人传习;又称《时宪书》面叶不宜列‘依西洋新法’五字,则为谠论”。
但黄丕烈对钱大昕跋中的“步算非专家”说抱有疑虑:“至于‘步算非专家’,余属尚之(李锐)详论其所以。”但李锐因被时任浙江巡抚阮元再次聘为幕僚,赴杭在即,因此“未及辨此,当俟诸异日尔”。虽未见两人续有讨论,但阮元《畴人传》对“步算非专家”说进行了辨析。该书由李锐、周治平协助编纂,初稿完成于嘉庆四年十月,约刻于嘉庆十五年,因此能代表阮元、李锐等的观点。阮元所见《不得已》,很可能即李锐携来。《畴人传》的杨光先传称:“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讥西法一月有三节气之新,移寅宫箕三度入丑宫之新,则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废也。”阮元等虽大体认同钱大昕的杨光先“步算非专家”说,但对杨光先部分历算学成就加以肯定,从“步算非专家”到“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废”,赞杨光先比钱大昕进了一步。
因阮元在学界的枢纽地位,《不得已》愈加扩散。例如阮元门生、姻亲许宗彦也藏有“《不得已》二本”。许宗彦是浙江德清人,嘉庆四年进士,阮元为其会试副主考官,许宗彦藏本应与阮元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如何看待杨光先及西学,孙星衍、凌廷堪间还爆发了一场争论。
孙星衍,字渊如,江苏阳湖人。他于嘉庆五年应浙江巡抚阮元之邀,佐理幕务,并主讲绍兴蕺山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嘉庆六年他致信凌廷堪称:“两年负米江淮,赖阮中丞招邀,不致有穷途之厄,行箧不能携书。”孙星衍在佐理幕务期间,很可能从阮元或李锐处获见《不得已》。他读后,激赏之余,径直为杨光先立传。该传虽未署时间,但结合孙星衍的生平及其与凌廷堪的通信等,它应撰于黄丕烈再发现《不得已》后。传中对杨光先倍加推崇,传后附有史论:
《孝经》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庄子》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论语》云:“盖有不知而作,我无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西法误会《大戴礼》“四角不掩”之言,而创地圆之说;误会诸子“九天”及《楚词》“圜则九重”之言,而创宗动天之说;误会岁差之言,而疑恒星有古今之差;变古“日月径千里”“月来食日”之言,而云“日体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东移,使其国土渐入离方。皆非先王之法言,圣人所不论。实则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系于此,必欲谈天穷所不可知,宁信各纬书及张衡、虞喜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亏南之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经异义》:“月高则其食亏于上,月上则其食亏于下。”是时日食在下,合之经义,自应亏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驯,而謇谔之节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西人以此敛迹,光先之功固亦伟哉!作为古文经学家,孙星衍这篇史论的特色也是“好古”。他先后征引了《孝经》《庄子》《论语》,以证明“先王之法言”的重要性和“穷所不可知”的不可取。他与认识到西法先进而主张西法源自或窃自中法的大部分“西学中源”说者不同,孙星衍认为西法是“误会”了《大戴礼记》、诸子、《楚辞》等中国经典原意,西人地圆说、宗动天以及对恒星、日食、北极星的解释,均不合于中国古圣贤之言。他指出“必欲谈天,穷所不可知,宁信各纬书及张衡、虞喜诸人有本之言”,杨光先难以驳倒西法,乃因他仅从历算出发而未从经学申论,没有抓住本源。孙星衍认为拒西法犹如拒杨墨,杨光先气节可嘉,可谓“圣人之徒”。嘉庆六年,孙星衍在致凌廷堪的信中,表达出类似观点:弟所为阴阳五行之学,取其考证经传,非古法不究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谓其同于语怪。后世之谈天有最不可通者,愿质左右:“日月径千里”之说,自是中法,且《白虎通》言千里畿法此制作;今则反之,谓日大于地数倍。夫日躔所在,《月令》名之“日在营室”云云,廿八宿每一宿相距不过几度、几十度,一度为二千九百余里。若云日大于地,则日在营室,左掩女虚危,右掩壁奎娄,且不止矣。此西人之戏言,不过欲乱吾中法,而江慎修、戴东原笃信之,江郑堂及吾兄亦颇助其张目。要知古学天文与算法截然两涂(下阙)孙星衍此信有阙文,残存的文字中虽未明确提及杨光先,但信中部分引证和论点,例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日月径千里”等,与《杨光先传》所附史论如出一辙,因此两者当存在关联(信或早于传)。孙星衍依据中国经典,认为日月直径相同,而非如西法所言日大于地、地大于月,他指责江永、戴震、江藩和凌廷堪被西人的戏言所骗,替西法张目。这引发凌廷堪的反弹,同年凌廷堪复信云:去秋奉到钧函,力扶汉学,辟西人推步为不可信,洋洋累牍,可谓好古情深、不徇众议者矣。……今年复蒙手书,来相督责……所驳西法数条,既不敢违心相从,亦不敢强辞求胜。良以合志同方,寥寥无几,不忍以一事岐辙,自启争端。第学贵虚中,事必求是,请略言之,可乎?窃谓主中黜西,前代如邢云路、魏文魁诸君皆然,杨光先浅妄不足道也。盖西学渊微,不入其中则不知。故贵古贱今,不妨自成其学,然未有不信岁差者也。岁差自是古法,西法但以恒星东移推明其故耳,不可以汉儒所未言遂并斥之也。再审来札所云:“天文与算法截然两涂。”则似足下尚取西人之算法者。夫西人算法与天文相为表里,是则俱是,非则俱非,非若中学有占验、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圆之说,则八线、弧三角亦无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诸实测,犹之汉儒注经,必本诸目验。若弃实测而举陈言以驳之,则去向壁虚造者几希?何以关其口乎?中西之书具在,愿足下降心一寻绎之也。从凌廷堪复信可知,嘉庆五年孙星衍即致信凌廷堪,以很长的篇幅抨击西法,该信的详细内容虽不可知,但两人显然此时已有较大分歧。一年后,孙星衍再次致信凌廷堪,于是有了凌廷堪这封复信。凌廷堪在信中径直批评杨光先“浅妄不足道”,则两人当曾论及杨光先与《不得已》。此前,凌廷堪在嘉庆二年致阮元的信中,已露出对杨光先的不屑,认为他“于天学全无所解……著《不得已书》,专攻西人之学,自命孟子”,语带讥诮,与孙星衍赞誉杨光先为“圣人之徒”形成强烈反差。凌廷堪复孙星衍信强化了这一论调,乃至将西学与汉学并举,主张“西人言天,皆得诸实测,犹之汉儒注经,必本诸目验”,两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凌廷堪认为汉学的核心精神是“实事求是”,西学与汉学是可以互通的。他还希望孙星衍放弃成见,静心研读几本西法之书。有意思的是,孙星衍《杨光先传》还激发焦廷琥撰写了《地圆说》一卷,可谓本轮《不得已》阅读风的副产品。焦廷琥是扬州大儒焦循长子,幼年即跟随其父研习历算学。嘉庆二十年,有人以地圆说求教于焦廷琥,而此人之所以发问,正是因为阅读了《杨光先传》:“客曰:是说也,吾固闻之,乃读孙观察渊如先生之文,而不能无疑焉。观察谓西人误会《大戴礼》‘四角不掩’之言,而创地圆之说,非先王之法言。以杨光先斥地圆之说,比孟子之距杨墨。”焦循、焦廷琥是地圆说的支持者,焦廷琥《地圆说》广征博引,论证地圆说在中国古已有之。朴学家们对杨光先及《不得已》的认识差异,投射出他们不同的西学观,反映出朴学在守旧与开新之间的复杂面向。二、杨光先作为晚清中西论争的“在场者”
经嘉庆年间由书籍发现而引发的阅读风后,杨光先又淡出士人视野。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基督宗教与西方科技再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杨光先所讨论的问题,重新成为国人需直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此时西强中弱的格局已经形成,形势比杨光先当年更为“严峻”。于是,杨光先与《不得已》再次回归,该书先是在苏州一带流传,后经王炳燮传入曾国藩幕僚及保守派领袖倭仁等手中。杨光先成为晚清中西论争的重要“在场者”。晚清《不得已》阅读风与上轮阅读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登场的关键人物是钱绮。他字映江,号竺生,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钱绮所藏《不得已》抄本,他自称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得见刻本于吴君寿云,时英夷适寇江南。杨公明见在二百年之先,一夕读遍,不胜骇服。价昂不能购,友人胡君子安,见之亦惊喜,欣然任钞录,即以赠余”。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江南的战事,对居于此地的钱绮、胡子安等造成一定思想冲击,当他们拜读《不得已》后,叹服杨光先有先见之明。吴寿云即吴根,与黄丕烈、黄寿凤父子友善。钱绮称吴根所藏《不得已》有钱大昕“手跋”,黄丕烈晚年财力不济,藏书开始陆续散出,吴根藏本应得自黄丕烈父子。钱绮在跋中称杨光先“正人心,息邪说,遏乱萌,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其书亦为第一有功名教,有功圣学,有功国家之书。……他日论辟异端之功,首列儒林,从祀文庙,未必不赖是书之存也”,并推许杨光先为“孟子之后一人而已”。钱大昕曾批评杨光先“步算非专家”,而孙星衍在赞誉之余,尚批评杨光先“文不甚雅驯”,但钱绮均加以回护:“明理不明数,公已自言之,何得为公病?书中辨论,未必无锋棱太峻语。然辟异端,不得不如此。圣人复起,亦当许之。”从钱大昕“不可谓无功于名教”,到孙星衍“圣人之徒”,再到钱绮“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孟子之后一人”,杨光先的形象越来越高大。钱绮并非昧于西学,他“酷好”同乡李锐之书,曾与张序均“讨论立天元诸术,成《苏城日晷表》一卷”。其《钝砚卮言》(1848)更征引了《天学初函》(李之藻辑)、《泰西水法》(熊三拔)、《地球图说》(蒋友仁)、《灵台仪象志》(汤若望)等不少汉文西学文献。书中指出“西术之妙在制器”,“西人目力之精,工作之巧,中国人万不能及”,“造器而使人可传,正见西人创法之善。又其图绘之精细,亦有不可及者”。可见他对西学的长处有一定认知,但这与他欣赏杨光先并存不悖,显示出历史人物的复杂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钱绮所征引者以明末清初时期的旧西学文献为主,而缺乏19世纪输入的新西学文献,则他对西学的认知仍停留于旧西学时代。他甚至称:“西洋人书译以中国字者,有汇刊之《天学初函》凡十余种,其书半述天主教,半为天文、算学、制器之书,彼国典册不过如是。”这从侧面印证出旧西学文本与知识遗产所具有的跨时空影响力,其在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内仍主宰着很多人的西学观。钱绮藏本成为晚清诸多藏本的祖本。例如南京图书馆藏同治八年(1869)《不得已》抄本,原为苏州画家顾大昌及其子顾曾寿所藏。顾大昌跋称:“此书绝少,向只管心梅先生(管庆祺)收藏一本,其中批注即其手笔。杨先生事迹,钱饮江(钱绮)跋语甚详。同治八年夏日,托刘泖生(刘履芬)借得,亟属江鹿门(江浩)手抄,数日而毕,汲汲遑遑,予心亦有所不得也。”则该书是顾大昌通过刘履芬借抄自元和人管庆祺。顾大昌在跋中将天主教目为“邪教”“邪术”,与钱绮态度相类。而顾曾寿跋称:“此书今日观之,字字金玉,后人当什袭藏好。设有遗失,得我此书者,亦当珍重。非予之愚,实在事关重大也。”可见父子俩对此书的珍重。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咸丰八年(1858)苏州华珂韵抄本,内含钱绮跋,其源头也当为钱绮藏本。前述钱绮藏本的流通范围尚限于苏州,促使《不得已》走出苏州者,是钱绮同乡王炳燮。王炳燮,字朴臣、璞臣,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任天津知县、邯郸知县。1929年柳诒徵曾幸获《不得已》抄本一册,“系王朴臣先生故物”,由苏州藏书家吴慰祖“沽自冷摊”,柳诒徵于是将其影印出版,化身千万。该抄本附有道光二十六年钱绮跋,则其源自钱绮藏本。王炳燮是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的积极传播者。王炳燮先是将该书传至曾国藩幕僚圈。曾国藩幕僚周腾虎咸丰八年四月十八日日记载:“又过王璞臣,携《不得已录》归。杨光先所著,辨天主教之言,惜学问不深,意正而文不足。”周腾虎从王炳燮处抄录得《不得已》后,很快又将抄本转借予赵烈文,赵烈文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日记载:“前于弢甫处借观《不得已录》一卷。”周腾虎,字弢甫,江苏阳湖人。他曾将同乡赵烈文引荐给曾国藩,赵烈文后成为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周、赵二人总体上较为务实与开放,周腾虎对清廷禁基督宗教并不以为然,认为应像对待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将教民编入户籍,听其自由信教,即重在制度化管理,而非视如洪水猛兽:“今西洋欲于内地造天主堂,我朝禁制之,其实汉构佛寺,明行回教,何害中国之大?有王者起,尽编其民于户籍,听行其所崇奉天主之教,西洋数十国指挥可定,何为是纷纷者哉!”周腾虎、赵烈文还对湖南新出的一部反教文献《辟邪纪实》(又称《辟邪实录》)持尖锐批评态度。周腾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载:“作书寄曾公(曾国藩)、左公(左宗棠)、恽次山方伯(恽世临),论《辟邪录》之谬。”赵烈文同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日记载:读无名氏《辟邪实录》一卷。书为湘潭人作,以辟耶稣教者。征引颇多,无如未得其要领。中国天地会等,虽原本彼教,而其淫邪荒诞,彼教转不若是之甚,举此以责彼教,彼教不受也。且彼教谬妄可指处甚多,不难使之失据。然中国儒者苟能昌明圣学,力敦己行,风俗之源一正,诸异端不辨自息。子舆氏所以必言拒杨、墨者,杨、墨之说精微近道,易以惑人,故几微之辨不可不急。若耶稣者,不必辨,亦不足辨也。卷后刻杨光先《辟邪论》,尚知体要。赵烈文从儒家立场出发,虽不认同基督宗教的教义,但认为该教的思想与社会危害性远低于天地会及杨朱、墨子,因此不必与之争长论短。他批评《辟邪实录》未得要领,只有其摘录杨光先《不得已》中《辟邪论》稍足可取。关于《辟邪实录》与《不得已》的渊源关系,下节再详述。周腾虎等对《不得已》《辟邪实录》的批评态度,引发曾国藩另一位幕僚——著名藏书家、贵州独山人莫友芝的极度反感,认为此系苏常人习气。莫友芝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载:“食后过眉(李鸿裔)、海(穆其琛)谈,弢甫(周腾虎)亦至,言有《辟邪录》极骂洋鬼之恶,意甚不平,殊不可解,大氐苏常人多此见也。”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莫友芝复向丁日昌倾吐此事:“晚过雨生(丁日昌),论今夏湖南所刻《辟邪宝[实]录》,播鬼子之奸恶,开人心之蒙昧,有补不小。昔杨光先为《不得已》一书,一时从鬼教者多自拔,而书中鬼之忌,鬼即重价购而毁之,此书即附此二文,而引据尤博洽,虽不无一二不当语,而语意危悚,其足以散从鬼教之顽民,而复其气,则可尚也。曾遇苏常间人,独痛抵[诋]此书,以为污蔑洋鬼,必为天地所不容,诚不知其何心也。”莫友芝对苏常人袒护“洋鬼”倍感愤慨。多年后,莫友芝同治六年至苏州、杭州收购书籍,在其《丁卯游苏杭收书簿》之后竟抄有《不得已》中《辟邪论》的部分内容,足见他对《不得已》一直非常激赏。曾国藩幕僚们围绕西人与西教存在明显分歧,这反映至《不得已》阅读史中,而思想分歧背后又夹杂着地域矛盾。王炳燮还将《不得已》直接上呈保守派领袖、大学士倭仁。杨光先跨越时空,参与到保守派与洋务派的中西论争中,倭仁、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等关键人物均曾阅及或论及《不得已》。先是同治二年,王炳燮致信倭仁,信中批评天主教有无父无母、无君、诬天、诬人、毁神、盗佛、灭绝祖宗、包藏祸心八大罪,听其传教则有动摇邦本、淆乱祖制、把持钱粮、贻累善良、败坏风俗、坏人心术、榛芜圣道、借资奸逆、盗窃威权、关碍国计十大害。因为王炳燮在信中多次征引《不得已》,或引起倭仁的注意。王炳燮于是将《不得已》誊抄一部并呈给倭仁,王炳燮称:《不得已录》一书,缮呈钧诲。窃思京师根本重地,异教肆行,并无防范,厝火之势,可为寒心。虽行教之人,未必遽萌叛逆,然自来叛逆之徒,无不借行教以纠众。况天主教公然无忌,愚民迫于冻馁,更易入其牢笼。其为政治之害,恐较回匪为尤甚。我中堂躬秉钧衡,当有默化潜移之术,俾隐祸得消,天下幸甚!王炳燮呼吁执掌中枢、海内人望的倭仁,能起而卫道,反对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教。倭仁有无从《不得已》汲取灵感,虽缺乏直接证据,但可从倭仁的盟友翁同龢身上窥见端倪。同治五年十一月,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聘请西人为教师,令五品以下的满汉科甲正途参与学习,遭致倭仁等的激烈批评。同文馆之争被称为“近代中西文化会面以后引起的第一场大争论”。这场争端以天文算学馆为导火索,后演变成文化、政治之争,与两百年前的康熙历狱如出一辙。而同文馆之争期间,时任翰林院侍讲翁同龢正在阅读《不得已》,翁同龢同治六年四月初九日日记载:“还汪慕杜《不得已》两卷”,“此抄本后竹汀先生、黄荛圃有跋。”汪承元,字慕杜,江苏甘泉(今属扬州)人,咸丰三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汪承元所藏《不得已》抄本有钱大昕、黄丕烈跋,则其源头也是黄丕烈藏本。翁同龢与汪承元在同文馆之争中,均站在抨击天文算学馆的倭仁一边,他们作为局中人,风波之时正传阅着《不得已》!相较保守派对《不得已》的一片赞誉之声,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却关注到康熙历狱所带来的深远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杨光先及后来朝廷公卿对西人、西技的排斥,是造成晚清中国军事科技大幅落后于西方的历史根源。他批评杨光先乃是见识短浅的“一孔之儒”,贻误中国“近百年”。据方濬师记载:江苏巡抚李公鸿章曰:“……杨光先者著《不得已》一书,极言天主教之害。其言谓宁可天算违行,不可任用西士,学士大夫亦交口丑诋,于是严行驱禁,毁其堂宇,西士绝迹于中土者近百年。然台官循其法不能变,军火利器依旧式制造,亦无奇巧变幻之方。孰意智巧之士,伏于海外,殚精竭虑,日新月异,其锋驯致不可当,而中国未知也。然其法既出,亦必不能深自藏匿。某考道光初年英吉利犹入贡,间有小巧火器,载在《礼部则例》。揆其意,盖隐然以此相炫耀。其时识者已为海洋抱隐忧,假令昔日体会仁皇帝圣人学于万物之意,去短取长,则天主教自不妨禁,西士自不妨留。梯航踵接,必有如南怀仁能为中国效力制造,尽其思之所至,变化出之,安见轮船、硼炮、洋枪、铜帽之独为外国擅绝也。至今日而杨光先《不得已》之论果何如哉?某每一念及,未尝不叹一孔之儒,贻误至此。”方濬师称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李鸿章担任此职是在同治元年至四年间,期间方濬师在总理衙门任职,故能闻得李鸿章的议论。有意思的是,王炳燮长期是李鸿章部属,李鸿章深知王炳燮思想保守,因此曾赐给王炳燮“美国人所著书”,希望其对西学深入了解后能改变认识,但王炳燮“读之终卷,辄不胜区区漆室之虑”,认为“火器为西人长技”,“岂可与之角其所长?”反映出他的迂阔。此后虽然随着《辟邪纪实》的流行,《不得已》的风头渐被盖过,但影响犹存,在清流派中尤其如此。例如宝廷曾撰文批驳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西方天文学著作《谈天》。宝廷与黄体芳、张之洞、张佩纶号称“清流四谏”,宝廷将该文寄予张之洞。张之洞在回信中,将宝廷比作杨光先,虽碍于情面,肯定其用意,却实则根本否定:寄示攻驳西学《谈天》一篇,用意极正,大可佩。与杨光先《不得已》一书,异曲同工。惟天算之术,究系专门,执事于推步未能燎[了]然,故攻击处尚未中其要害。……尊意大抵于天算则主中而驳西,于经学则抑汉以申宋。……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岂非快事、便宜事!何为反攻之乎?天旋、岁差诸条,西法固精,即使错谬,于实事何害?此不足为中国患者也。该信作于光绪十五年至十六年间,张之洞正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在西学问题上,与昔日清流派同僚宝廷出现分歧。张之洞对杨光先及宝廷的做法并不认同,他不仅承认在天文算学上中法不如西法,而且主张西法应为中国所用而非为中国所患。他秉持实用主义态度,试图调和中西与汉宋之争。他称宝廷之文与杨光先《不得已》“异曲同工”,可谓欲抑先扬,明褒实贬。此外,“清流四谏”之黄体芳及其子黄绍箕,在光绪十一年初中法战争期间,也积极传阅着《不得已》。《不得已》不仅被阅读、传抄,光绪十五年吴地还刊刻了《重辑不得已辑要》一卷。该书开篇以朱字录有雍正帝《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条及道光十九年颁布的《钦定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四言韵文》。正文分“原目”“原刻本附”“重辑本附”三部分:“原目”辑自《不得已》的《请诛邪教疏》、《与许青屿侍御书》和《辟邪论》;“原刻本附”含《改天主堂为天后宫记》(李卫)、《日本世宏论邪教攻心》(摘自盐谷世弘《隔靴论》)和荆楚挽狂子跋;“重辑本附”则含《杨光先传》(孙星衍)、《曾文正公书示逆夷威妥玛》(曾国藩)和《湖南阖省公檄》。刊刻者称:“秋试在迩,急于竣工分贻同好。昨从友人处觅获《不得已》上下两卷,原书并《辟邪实录》等箸[著]不及刊布,拟试后集赀续刻。”则他当为吴地生员。该书在《不得已》基础上杂糅了后世各种反教文献,旨在借助皇帝、日本人、孙星衍、曾国藩等中外权威话语强化其反教的合法性。三、启蒙的背面:从《海国图志》到《辟邪实录》
研究书籍阅读,不应局限于书籍本身。例如法国学者丹尼尔·莫奈在18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收集汇总的2万册图书中,仅发现1册卢梭《社会契约论》,那么《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否被高估?达恩顿指出:莫奈“忽视了《社会契约论》通俗本,尤其是卢梭《爱弥儿》第五卷内的通俗本,在法国大革命前就是毋庸置疑的畅销书。”思想犹如涟漪,第二圈的波及范围常比第一圈更广。《不得已》在19世纪主要以抄本形态流传,直接的读者毕竟有限,但如果扩大阅读史的视域,将间接流传纳入考察,则受众面有待重估。湖南思想家魏源及其《海国图志》被视为晚清“开眼看世界”的代表,这固然不错,但启蒙的背面并非没有幽暗之处。在历史转折时代,鲜有纯粹的启蒙或保守思想家,启蒙与保守若互为消长的阴阳两面,我们需正视历史人物及文本的复杂性。当文本的内容多元而开放时,由于读者知识背景、阅读目的与认知能力各异,对同一个文本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解读。《海国图志》既是晚清中国读书人认识新世界的窗口,又是中国及日本、朝鲜反教运动的凭依,而杨光先的身影隐现其中。《辟邪纪实》(《辟邪实录》)是晚清影响最大的反教文献之一,咸丰十一年初版,同治元年增订再版,同治十年、光绪十二年重刻,共三卷附一卷,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书中多淫秽、暴力之词,主要采用捏造与传播谣言的方式反教,例如污蔑基督宗教宣淫采战,散瘟放蛊,以及窃取眼睛、肾子、心肝、脑髓、子宫、乳头与辫发等。《辟邪纪实》的理论水平虽远低于《不得已》,但煽动性更强。它成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在中国各省广为流传,1870年还被传教士译为英文。它屡遭西人抗议,例如光绪十三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照会总理衙门:“前于一千八百七十年间,有人编著极污秽《辟邪实录》一书,遍传各处,经贵衙门严行禁止销毁在案。兹复有人印刷此书,在中国遍处布散。其中言语极其污秽,最足激动人心,滋生事故……闻其在北京续印此书,仍欲布散。”可见该书流传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然而鲜有人注意到,它竟与《海国图志》有密切关联!崔暕是《辟邪纪实》的实际编著者。崔暕,字晦贞,湖南宁乡人,早年以秀才身份加入湘军,后成为胡林翼、左宗棠幕僚,光绪元年中举,曾任贵州仁怀知县等。其同乡周汉的反教思想,即深受《辟邪纪实》影响。该书收录有杨光先《辟邪论上篇》《辟邪论下篇》,但上篇实际摘自《不得已》卷上《与许青屿侍御书》,而下篇才摘自《不得已》原书中的《辟邪论》。崔暕并未阅读过《不得已》原书,其《辟邪论》上下篇乃转抄自魏源《海国图志》。因为《辟邪纪实》所节录的《不得已》与《海国图志》本内容、结构均相同,绝非巧合。实际上,《辟邪纪实》与《海国图志》渊源颇深,该书所引《景教考》《烈皇小识》《坤舆图说》《澳门纪略》《西域图志》《每月统纪传》等论著,基本可断定也是转录自《海国图志》。但全书仅有一处,明确标注其参考文献为《海国图志》:曩京师有医某者,岁终贫困,思惟入天主教可救贫,而邪教又不可入,乃先煎泄药升许,与妻子议言:俟我归,如惛迷者,急取药灌我。于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以金,归家则手掷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药,良久暴泄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教师至,手执利刃,索还原物。医言:必告我何物,乃相还。教师曰:此天主圣母也,入教稍久则手抱人心,终身信向不改矣。乃还之去。(《愚溪文稿》及《海国图志》)这段文字,虽注明出自《愚溪文稿》及《海国图志》,实则完全转录自《海国图志》,《愚溪文稿》系杜撰之书。又如书中另一处注明出自《西樵漫笔》,实则也转录自《海国图志》,《西樵漫笔》同系杜撰之书:有武生王文沐者,豪士也,闻从其教者,人死必骗取眼睛,欲试其术,乃佯入教中。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王奋起击之,随追至其家,刃其首,并毁其耶稣像。其事闻之京城,上厚奖之。(《西樵漫笔》)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崔暕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炫耀其博学,前述莫友芝即夸赞《辟邪纪实》“引据尤博洽”;二是为显示《辟邪纪实》的“纪实”性,表明书中内容乃共识而非私见,可收到三人成虎的效果。因此,他还煞有介事地附录了《辟邪纪实考证书目》,罗列参考书达202种(书目后按语又提及8种),以张大其词。崔暕所引《海国图志》,均出自该书“天主教考”。《海国图志》存在五十卷(1842)、六十卷(1847)、一百卷(1852)三种版本,而“天主教考”的相关内容自五十卷本即有,可见魏源对此持之甚坚。魏源在摘录《辟邪论》后附有按语:“福音书耶稣自称为上帝之子,而称上帝为神父,未尝谓耶稣即上帝也。此所论稍未中肯,其余大概得之。”他和杨光先在反教上是一致的。在《辟邪纪实》这一案例中,《海国图志》既是杨光先反教思想的传播者,又是迷魂、取睛等部分谣言的权威源头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魏源不仅未启崔暕之蒙,而且为他反西教乃至反西技提供了思想资源。正如谭嗣同所言:晚清时期,湖南既“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又以“精解洋务”闻世。魏源已导其端。此外,晚清西北史地学名著——何秋涛《朔方备乘》中杨光先《辟邪论》也转录自《海国图志》。而福建诗人林昌彝的反教名篇《辟邪教议》,将《海国图志》所引《辟邪论》视为最核心的论据。又如李慈铭对《海国图志》“天主教考”亦青睐有加,并特别赞赏《辟邪论》,他在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感慨:点阅《海国图志》。魏氏此书体大思精,真奇书也。其采杨光先《不得已》中《辟邪论》上下篇,又自为论,以抉天主教之妄。……当魏氏此书初出时,使朝廷先加意此事,密谕地方大吏饬郡县官,日讨国人而申儆之,毋使其陷溺,事犹可为耳。今西洋罗马之教王已拥虚器,德国又扼之甚力,英俄诸国袖手旁观,惟法夷拥护之,而其愚弄中国,则仍并智一心,可叹也。《海国图志》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面对开国后基督宗教的冲击,净土宗僧侣养鸬彻定成为19世纪后半叶日本反教运动领袖。他曾翻刻明末反教文献《辟邪集》,并著有《辟邪管见录》《笑耶论》《释教正谬初破》《释教正谬再破》《佛法不可斥论》等多部反教书籍。而他所阅读的《不得已》,即出自《海国图志》,其《辨道书目提要》著录有“《辟邪论》一卷,《海国图志》中抄出”。他在《释教正谬初破》自序中也称:“挽近西夷倡邪教,诱掖世人,然未若我佛教之广流传四海也。《海国图志》备载焉,不待吾言也。”将《海国图志》视为佐证其反教主张的权威文献。迟至20世纪,韩国李晩采所编反教文献《辟卫编》,仍将《海国图志》所载天主教“奸诱妇女,诓骗病人眼睛”等内容录于书末。启蒙与保守犹如《海国图志》的一体两面,如影随形。正如浏阳生员罗棠所言:“服言既异,隔阂易生;畛域未融,猜忌难泯。于是有挖目取心之谣……儒生撰著,漫不加察,虽以顾亭林、魏默深之鸿博,犹误采入《天下郡国利病书》《海国图志》中,三复白圭,一言不智,吾不能为贤者宽矣。”《不得已》借助《海国图志》《辟邪纪实》等书的层层转录,在东亚反教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四、结语
受进化史观影响,学界研究国人西学阅读史,多侧重“进步”书籍,而对“落后”书籍相对忽视,更鲜有将明末清初与晚清反西学文献结合考察者。鲁迅指出:“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些“过时的书”,在某些时期或某些读者身上,影响未必比“进步”书籍小。在19世纪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中,《不得已》既是西学派的“负遗产”,又是保守派的正面思想资源。《不得已》在19世纪的阅读史可粗略分为两期:鸦片战争前,主要表现为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与评论;鸦片战争后,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得已》的意义被重新安放,杨光先渐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与符号。杨光先的幽灵不仅从未远去,而且还跨越时空成为19世纪中国乃至东亚近代化的参与者。相较《破邪集》《辟邪集》等其他反西学文献,《不得已》因兼具反西教与反西技双重属性,故在流传过程展现出宗教与科技之间的复杂纠缠。杨光先的支持者们,有的只反西教不反西技,有的既反西教又反西技,个体间重心与程度互有异同。晚清随着新西学的输入,杨光先的历算学趋于过时,而反西教层面借助《海国图志》《辟邪纪实》等得以强化。虽然反西教者的构成与背景极为复杂,但以崔暕为代表的极端式反教,不仅会招致教案,而且易发展为一种笼统的排外主义,对中国走向世界显然不利。桑斯坦曾提出网络时代的“信息茧房”问题: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信息进行选择与过滤,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在前网络时代,同样存在类似的信息茧房。达恩顿注意到,有一种阅读“只是辨认出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不是获取新知识”,因此,“阅读并没有开拓人们的知识领域,而很可能只是重复封闭的知识体系”。《不得已》阅读史即生动例证。对有些读者,即使将一部《海国图志》置于面前,其所见仍然只有杨光先,此为阅读史的魅力所在。阅读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历史研究中应避免将一部书标签化。文本一旦生成,很大程度即摆脱了作者的控制。“进步”书籍,可能读出“落后”;“落后”书籍,可能读出“进步”。何况很多书籍,本是一体两面。《金瓶梅》既可诲淫诲盗,也可度脱众生;《海国图志》既可传递新知,也可播撒愚昧。一部书的阅读史,即一部多彩的思想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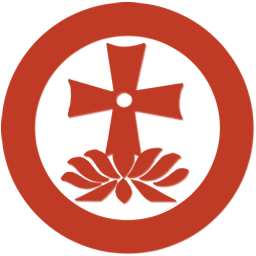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