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普遍认为福音是认知基督教问题的一把钥匙,前辈学者深耕于基督教文献的史实考证与文本梳理,但对福音概念生成流变过程中的复杂性关注不足。天主、上帝以及宗教等相关概念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研究方法可主要归于以下两种路径。一是语词翻译过程中的“观念旅行”,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讨论概念谱系的形成,如日本学者柳父章对“神”“上帝”等概念的翻译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孙江对“宗教”概念和传教士中国宗教观的考察。二是集中讨论礼仪之争和译名冲突,如从《圣经》文本考察译名的误读及其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接受。
以福音为中心的研究仍然不足,爬梳与厘清此译名背后概念的历史十分必要。本文将运用德国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所有概念都是历史集合体,虽然基本概念会出现含义的反复,但它不应该被永恒的观念或问题所限制,因此,每一个基本概念都有潜在的历史性变化。语词(word)和概念(concept)之间本应具备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但在具体的使用中,往往旁生歧义。支撑语言存在的文本成为了勾连语词和概念的媒介。福音概念的译介在保持本真性和适应新语境之间左右摇摆,在跨文化和跨语际的实践中日渐成型。
本文试图借鉴天主、上帝、宗教等上位概念的研究范式,对“福音”这一下位概念做历史语义学的梳理。简言之,福音译介与传播历经三个阶段:在早期耶稣会士的《圣经》文本中,福音概念被音译为“万日略”;以“万日略”为主,“福音”为辅,则延续到了17世纪末;此后,《圣经》文本的普及,尤其是二马译本的出现,标志着“福音”译词的正式确立。在对历时性与共时性文本的分析中可见“福音”概念最终定型。
福音这一译词的初诞,与汉译《圣经》密不可分。由此需考察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神学著作和18世纪以来的《圣经》汉译本。虽然这些译本成文年代不一,文体各异,但其内在义理的同源使理解汉语福音概念变迁成为可能。下表即本文所使用的文本:
表1 早期天主教与基督教传教士信仰著作与《圣经》译本
二、“Evangelium”=“万日略”?
围绕“福音”这一新名词的出现,本节将分析17-18世纪四位天主教传教士的五个文本,以及在拉丁文词源“Evangelium”的汉译问题上所展开的论争。这些译本在时代背景、内容择取、语词翻译和修辞文理等方面各具特色,而音译还是意译,是许多传教士翻译福音概念面临的首要难题。
1、以译为述——《口铎日抄》与《天主降生言行纪略》
《口铎日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著经典。其中多次出现的《万日略经》,即今日的福音书,是口铎者反复引用、劝诫信徒、警醒世人的重要文本。就目前所见文献材料,艾儒略当为译介汉语福音概念的第一人。
艾儒略著述颇丰,所著《天主降生言行纪略》(1635)为记载《圣经》四福音书故事的译述作品,也是最早讲述耶稣生平事迹的汉译文本,全书开篇《万日略经说》是继《口铎日抄》后研究福音概念的重要文本:
造物主圣教,有古经,有新经。古经乃天主未降生启示先圣,令传溥世,即以将降生事旨豫详其中。新经乃天主降生后,宗徒与并时圣人纪录者。中云万日略(译言好报福音)经。
此处,“万日略”是“Evangelium”一词的音译,取“好报福音”意。“经”是记载耶稣降生、受难、复活、升天事迹的真典。艾儒略认为《万日略经》是四圣共奉的信典,即今天的《四福音书》。前述《口铎日抄》常征引《万日略经》,可见艾氏对福音书的喜爱。艾儒略中文造诣极高,他为何要生造“万日略”这一略显拗口的音译词,并以“福音”作为“万日略”的补充说明,重审《天主降生言行纪略》这一文本,或许能管窥艾儒略的翻译动机。
今将四圣所编,会撮要略,粗达言义,言之无文,理可长思,令人心会身体,以资神益,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云译经也。
此降生纪略,止约识吾主耶稣所经之迹,与所垂之训而已……吾主耶稣事实,原系四圣所纪,彼详此略,有重纪,有独纪者。兹特编其要略,不复重纪详尽,若夫全译四圣所纪,翻经全功尚有待也。
上述两段引文可视为艾儒略对《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一书的定位,艾氏援引《约翰福音》末节对《圣经》的看法,指出此书是对四福音书的摘录。不敢妄言“译经”,不仅因为此经之特殊,也因为他深知摘录与翻译全经的差异,故自称“西极耶稣会士艾儒略译述”。纵观全书,艾儒略开创了一条“以史代经”重构天主降生故事的新方式,以译为述,看似述,实为译,其所译并非经书,而是历史。可见,艾儒略生造了“万日略”这一对福音以另类诠释的译词,是他希望将个人诠释融入汉语语境的叙事中。
2、文本新释——阳玛诺《圣经直解》
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可考事迹很少,但撰译校订之书颇丰。与前人转译福音书不同,阳玛诺的《圣经直解》几乎“直译”了福音书中的经文。全书以天主教的主日和瞻礼为线索,遵循释名、引经、解经、箴言的体例,解经的篇幅往往是原典的几倍。徐宗泽评价此书“文理古雅,诚一本好书”。陈垣则认为阳玛诺的《圣经直解》、《遵主圣范》采《尚书》谟诰体,与寻常著述不同,足以显其高古也。
阳玛诺始终强调自己并无全译四福音书的意图,不过是译述旧闻,抒发胸意。他以中国传统的经典重新诠释《圣经》,文体修辞颇有古风。在文本新释的叙事框架下,阳玛诺是这样诠释“圣经”与“福音”概念的:
圣经原文谓之阨万日略,译言福音,乃天主降生后,亲传以示世人者,即新教也。
阳玛诺的诠释,颇有将“圣经”“阨万日略”“福音”相等同的意味。这一叙事方式虽有偏颇,但阳玛诺有他自己独特的考量,“虽圣史各有所载,同归一理,则圣经犹一也。”各经同归一理体现了阳玛诺试图弥合语词的内在差异性,将其纳入统一的论述体系中。然而,阳玛诺的叙述不乏前后矛盾之处,上文将“圣经”等同于“阨万日略”,下文却将“阨万日略”视为“圣经”的一部分:
终问阨万日略,与圣经,何以异?曰:圣经,公名也。或天主亲口所论,或天神代主所传,或先知圣人得天主默照所示。俱事,而命圣史纪载,以诏后世者,乃称阨万日略,而为圣经之一分。
如何理解“阨万日略”与“圣经”的关系?此处“圣经”实指与古经相区别、记载福音故事的新经,而“阨万日略”是“圣经”所含的下位概念,但有时可“以偏概全”,隐喻《圣经》文本传递出的好消息。
“圣经”“阨万日略”“福音”三者在概念上有别,“阨万日略”与“福音”的关系非常微妙,可视作同一概念的两个不同面向。四圣史所记“福音书”被提前为“阨万日略”,而《圣经》所载耶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被喻为“福音”。阳玛诺并未对“福音”和“阨万日略”的概念加以严格框定,但他注意到教义层面上“福”的重要性,如其花大量笔墨阐述的“八福”。“福”让人恒美至善,崇敬天主,“福音”则为耶稣复活后拯救世人的好消息,“避永苦、享永福”的教义恰恰契合了中国信徒求福免祸的心理。与“阨万日略”相比,“福音”译词渐渐占得上风。“福音”概念逐渐从四福音书的范畴扩展至整个《圣经》文本,这也是阳玛诺译本与前述艾儒略译本的很大不同。
3、文本普及——白日昇译本
以“万日略”为主,“福音”为辅的用词现象延续到了17世纪末。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在福建长乐发布七条禁令,其核心为禁用“天、天主、上帝”等字样形容天主教的万物之主,改用音译名“陡斯”(Deus),甚至禁止一系列祭孔祭祖行为。这一行径招致耶稣会士的强烈不满,礼仪之争一触即发。同为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昇(Jean Basset,1622-1707)的态度本应与颜珰保持一致,但1701年他公开质疑颜珰的“七条禁令”,因不愿卷入差会之争,白日昇主动请缨,远赴四川布道。
白日昇入蜀后,经年致力于翻译《圣经》。但1707年白日昇的突然病逝,使得他和助手徐若翰合译的《圣经》,在行进至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与保罗书信时戛然而止。现存白日昇译本分四福音书合编本与四福音书单列本,本文拟参照成书时间最早的罗马本(意大利罗马卡萨纳特图书馆馆藏本),尝试将1704年白日昇所译《四福音书》与前述阳玛诺《圣经直解》做文本比较:
《玛窦攸编耶稣基督圣福音》第十一章(白日昇)
若翰既居囹圄,闻基督之行,使厥徒之二,往询之曰:尔为必来者乎,抑尚他望乎。耶稣答之曰:归告若翰,以攸闻攸见,瞎者明,瘸者行,癞者净,聋者听,死者复活,贫者受福音。
《经圣玛窦》第十一篇(阳玛诺)
维时若翰居囹圄,闻契利斯督异行,召二徒往询曰:尔其当来人,抑尚望他来。耶稣语曰:归告若翰,以攸闻、攸见,瞎者明,聋者听,瘫者行,癞者净,死者活,贫者受教福音。
上述两个译本除“基督”译名不同,以及《圣经直解》在开篇使用“维时”二字增强节译的叙事感外,文本差异较小。两译本是否共同参考了某一底本,抑或白日昇本参考了阳玛诺本,目前尚不可考。但白日昇译本是现存最早的《新约圣经》汉译本,白徐二人逐字逐句对照原文,以期准确、忠实地再现《圣经》思想。而《圣经》汉译也逐渐摆脱了早期节选、意译式的翻译,开始大规模地集中于直译。
在白日昇四福音单列本中,“福音”一词共出现20次,作名词使用的“福音”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白日昇并未直接音译“万日略”,而选择了与中国文化更有亲和力的“福音”,来对等翻译西方原有的宗教语汇。笔者推测,“福音”一词的选定与使用极有可能受到四川文士徐若翰的影响,徐对白日昇译本的成书至关重要,他了解“福”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美之意,而“福音”既能准确地传达基督教教义,又能积极地响应中国信徒的心理需求,可谓两全其美。“福音”译词在18世纪初期的《圣经》文本中开始普及,而白日昇译本将会对一个世纪后的新教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回归与遗弃——贺清泰之《古新圣经》
《圣经》译本的影响力不仅与文本的翻译相关,更直接地体现在其普及范围。前述白日昇译本在辞章、义理上堪称18世纪汉译《圣经》的巅峰之作,但其价值与影响在成书之初被严重埋没,各差会对待汉译工作的态度与神学思想的差异,对于译本的流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随着1800年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1735-1813?,Louis Antoine de Poirot)《古新圣经》的问世,官话直译风潮兴起。
《古新圣经》为一部文白兼备的集大成之作,徐宗泽所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开篇即收录《古新圣经》,作者用浅近的文言、混杂北方官话,完成了庞杂的《圣经》汉译工作,此书完全按着《圣经》的文本本意,不图雅驯。在夹杂着“呢”“么”等语气词及儿化音的北京土白中,“万日略”重回《圣经》文本,与“福音”并驾齐驱:
……用如德亚话纪了此经,名万日略,此名恰好,若解万日略的意,即福意。(天主)…也要赐己福音我们,能有比这福的音么?此福音事,不单在万日略经内,还因是天主圣神的特工…
“福的音”这一表述虽显口语化,却贴近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贺清泰对“福音”与“万日略”译词的内涵与外沿做了明确区分:“万日略”指经名,特指四福音书;“福音”不仅是万日略经所载好消息,更是天主降生带给世人的嘉美之言,福音概念外延的扩展继承了阳玛诺译本的特色。在《古新圣经》的文本中,“万日略”取代“福音”成为全书通用的固定译词,现对比如下。
表2 白日昇四福音单列本所见“福音”与贺清泰《古新圣经》所见“万日略”
翻译《圣经》的人,虔诚敬慎,惟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文理的说法,他们不按各人本国文章的文法,守全按着《圣经》的文本本意,不图悦人听,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自古以来,圣贤既然都是这样行,我亦效法而行。
由此可大致了解贺清泰对译经所秉持的审慎忠实、不取悦于人的原则,因循前人、效法而行,回归“万日略”译词其实更符合《圣经》原典的初衷。但因《古新圣经》从未刊行,流传不广,此后“万日略”最终湮没无闻。
“福音”概念形成之初的音译词“万日略”经历了生成、传播并最终湮灭的过程。从艾儒略以译为述、以史代经的翻译策略,到阳玛诺直译文本、以经解经的诠释方式,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圣经》汉译并未倾注太多精力,传教重点也不在翻译工作上。白日昇译本与贺清泰译本虽各以“福音”和“万日略”诠释Evangelium,但因流传有限,译本自身的价值与传播效能并不相称。上述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揭示出自明末以来,《圣经》文本从节译、音译转向全译和意译的翻译趋势。最终,早期被用来诠释“万日略”一词的“福音”概念后来居上,逐渐成为汉译《圣经》的既定用词,并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文本中得到真正普及。
三、“福音”概念的确立
17世纪末18世纪初,围绕“Evangelium”如何翻译所展开的论争告一段落,此后,“福音”概念在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所译《新约圣经》中逐渐定型,二马译本被奉为汉译《圣经》之经典与权威,下文拟对二马译本中的“福音”做一简要梳理。
1、“嘉音”与“福音”
1799年10月,马士曼历经五个月的海上漂泊,远渡重洋,自赛兰坡登陆,开启了在印度的传教事业,这位传教士终其一生在印度传教,从未踏足中国。但作为《圣经》汉译史上“二马之争”的当事人,他与“福音”概念的译介和传播密切相关。
1810年,第一个新约《圣经》单行本《此嘉语由所著》问世,随后《此嘉音由嘞所著》出版,上述两译本即为人熟知的《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从福音书名便可看出两译本的晦涩难懂,彼时马士曼手头并无可参考的底本,人名、地名、神学词汇多由马士曼与助手拉撒尔(Joannes Lassar,1781-?)生搬硬译。
“福音”在此被译为“嘉语”“嘉音”,“嘉”与“福”同样带有好消息、好运气之意,马士曼选用“嘉”字,应与助手拉撒尔有关,拉撒尔自幼学习中文,受粤语文化圈浸淫颇深,“嘉语”“嘉音”在粤语中颇为悦耳,极有可能是马士曼初学中文之时,边学边译之作。虽然中西言语相异,语音有别,翻译水平及准备工作的不足造成了此译本的诸多缺陷,但马士曼对“福音”概念的理解与翻译基本到位。
马士曼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与策略,其《若翰所书之福音》(1813)及《圣经新旧约全书》中的译名与后来的通用译名大多吻合。学界对二马译本的关系已有诸多考证,多数学者认为马士曼与马礼逊译本高度相似的原因在于两人共同以白日昇译本(斯隆本)为蓝本,并不存在谁抄袭谁之说。马礼逊本人也不讳言,自陈其所译《新约全书》参照了一个天主教神父的手稿,只是在马礼逊——来华新教传教士第一人的光环笼罩下,学界对马士曼的关注较少。现试对马士曼的《此嘉音由嘞所著》、《圣经新旧约全书》,及马礼逊的《神天新遗诏书》做一节译比较:
表3 马士曼、马礼逊译本中的“嘉音”与“福音”
2、英华、华英字典所见“福音”
语词、概念既定化的另一个表征为字(词)典的收录与记载。字(词)典对于语词的解释往往简单明晰,一目了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也象征着语词使用在文本中的固化。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华英字典逐渐增多,这些字典不仅是传教士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风俗的必备工具书,也为《圣经》汉译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二马译本问世后,“福音”概念在马礼逊及后人编纂的华英、英华字典中得以成型。
1815-1823年间马礼逊编纂的三部六卷本《英华字典》为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该字典采用英汉对译的方式。马礼逊《英华字典》对“Gospel”给出了明晰的译词——“福音”,指好消息、早期耶稣会士传布的福音,以及传道和传福音的活动,凸显了“福音”概念的实践色彩。继马礼逊之后,麦都思(W.H. Medhurst,1796-1857)《英华字典》将“福”释为极好的、幸运的、快乐的,麦都思对“福”的认知更进一步,以古汉语中的“害盈福谦”解释福祸之间的此消彼长。五年后,“Gospel”的对应译名添列“嘉音”一词。
19世纪70年代,罗存德在麦都思字典的基础上,编纂了颇具权威、对各国影响深远的《英华字典》(1866-1869)。罗存德字典中,“福音”概念的意涵得到扩展,并呈现出三个面向——传道宣教层面的福音,宗教信仰层面的福音和被视为真理信条的福音。同时,“Glad”条目之下的“glad tidings”,罗存德并未将其直译为“好消息”,而是代以“福音”,可见到19世纪中叶,“福音”概念及其扩展意涵逐渐确立,此后,福音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但仍以基督教教义与实践作为基础。
从《圣经》文本到英华字典,“福音”概念的尘埃落定,标志着其在语词层面上的固化,作为“evangelium”的对等译词,“福音”既传递出了四福音书原有的嘉美意涵,也契合了中国信徒对“福”的追求。在“福音”译词的确立过程中,虽然一度出现了“万日略”一般的音译,或“嘉音”等同样表征好消息的意译,但最终,英华字典仍以“福音”为主,字典的权威和普及使得“福音”译词的面向日益宽广,使用日渐普及,并最终从语词走向概念。
四、从语词到概念
二马译本标志着福音译词的确立,英华、华英字典象征着其使用的普及,福音概念成型后,其在后续文本中的后续变化也要关注。此外,早期文本的考察对象多为汉译《圣经》,随着文言分离趋势的日益明显,传教士对文本的编纂逐渐走向地方化,随之而来的是官话译本和方言著作的大规模涌现。在这一背景下,福音概念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如何?
1、历时性视野下的汉译《圣经》
荷兰宣道会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1803-1851)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是目前颇为稀有、学术价值极高的《圣经》汉译本。太平天国的《新旧遗诏圣书》便是对郭实腊译本的重新修订,两译本相似程度极高。委办译本是19世纪40年代十余位传教士倾十余年的翻译成果,虽然由于各差会及传教士间的分歧,委办译本最终未能达成统一中文译本的初衷,但此译本仍是《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掀起了《圣经》汉译之新潮。同时比较这三个成书于19世纪40-60年代的译本,有助于在历时性层面对“福音”概念的变迁做一梳理。
郭实腊与太平天国译本均选用“嘉音”一词,委办本一致选定“福音”。可见,二马译本虽为新教传教士《圣经》汉译之滥觞,但“福音”在文本中的普及不是一日之功,仍然有一个传播与接受的过程。细察19世纪40-60年代的译本,与“福音”搭配的语词越来越多,比之二马译本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如郭实腊译本中的“神国之福音”、“基督之福音”,委办译本中的“上帝国福音”,等等。这些与“福音”搭配的短语揭示了“福音”在文本中的历时性变化,以及“福音”指代的多元化。
2、官话译本中的“福音”
19世纪中叶,福音从语词到概念的另一个转向表现为出现了大量通俗文本。早期传教士所译《圣经》,并未采用官话(白话),他们认为官话(白话)不够严谨,有失《圣经》的权威性。但面对文言分离的趋势,《圣经》文本与传教实践之间产生了龃龉,传教士们不得不编纂一些方言译本与著作,来应对布道所需。
1728年,雍正下令定北京官话为正音,洪武正韵的南京官话时代就此结束,但在18-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官话的使用范围与流行程度仍然很广。如1856年由麦都思、施敦力合译的《新约全书》是首部以官话译成的汉语《圣经》(下文称南京官话译本),其中不乏“福音”一词的身影。
瞎眼的就能够看见,折脚的能够行走,麻风的能够洁净,耳聋的能够听见,死亡的能够复活,贫穷的能够听福音。(马太福音11:5)
约翰用许多说话,解劝安慰人,报好消息给百姓听。(路加福音3:18)
南京官话译本与委办译本的出版时间非常接近,在上帝、基督、福音等译名和人名、地名的使用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其文理和语体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原有的文言韵律被打破,定语修饰成分的增多使得口语化色彩加重。出现了以白话“好消息”解释“福音”的现象,这也是“好消息”首次出现在《圣经》汉译本中。由于南京官话译本直接将文言译本进行转译,不太注意语言的铺陈和辞章的修饰,因而其历史价值远高于文本价值。十余年后问世的北京官话译本,译文流畅,辞章通达,“不易为别的译本所胜过”,这一译本真正实现了白话从口语体向书写体的转变。“福音”一词在文白对照中的含义变化不大,但文本中的“福音”由繁入简,走向口语化。
3、“福音”与《圣经》三字经
相较于形式固定、体例严谨的《圣经》,自18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套用中国传统文体的布道小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圣经三字经与七言诗。最早尝试编纂圣经《三字经》之一的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麦都思,早在1823年,他便在巴达维亚编印出版了《三字经》,共17页,948字。笔者未能得见麦都思早期的《三字经》译本,本文所举是1856年墨海书院《三字经》本,共17页,960字:
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
我信之,可得救,凡尔众,无富贫,必悔罪,信福音,改前非,向真道,如是者,为从教。
季度奖《三字经》的文本内容大同小异,但其内含的传教方式十分特别。卫三畏认为“以《三字经》形式撰写的成千上万本基督教真理册子,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中得以传布,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与直接阐述教义的宣教作品和读起来略显枯燥乏味的《圣经》文本相比,《三字经》的文体更利于传教士布道和信徒记忆,其行文讲求平仄押韵,对识字的要求也不高,基本教义概念能够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现。这类《三字经》文献沿袭了中国传统三字经所发挥的启蒙幼学的社会功用。随着浅文理白话译本的流行,与《圣经》相关的通俗文本层出不穷,此后,“福音”逐渐脱离单一的宗教文体,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意涵,也反映了基督教在华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五、结语
17-19世纪《圣经》文本对“福音”的诠释揭示了“福音”概念的确立过程。相较于天主、上帝等上位概念,有关“福音”译介和使用的争议较少,汉语语境中的“福音”并非一个语义剧烈变动的概念。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际,对“福音”这一新名词的诠释大多停留在翻译层面,尤其着眼于对《新约圣经》开篇四福音书的节译,就语词的翻译而言,无论是被放弃的“万日略”抑或昙花一现的“嘉音”“嘉语”,都不如“福音”来的贴切。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初,二马译本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境中“福音”译词的正式确立,“福音”取代“万日略”“嘉音”等,成为了基督教专用语词。19世纪末,随着与“福音”相关的英华字典的出版和通俗译本的普及,“福音”译词的受众日益扩大,汉语语境中的“福音”被赋予了强烈的实践性色彩,真正完成了从语词到概念的转变。一度被选择性翻译的“福音”,几经变迁,最终成为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概念,以及普通信徒走进基督教的基本门径。
时人之所以选择“福音”作为对等译词,不仅因为它是一个被创造的新兴语词,概念的混淆和误用较少,更考虑到“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厚内涵,带有中国式信仰色彩的“福音”更贴近中国人礼神致福的信仰结构。然而,“福音”概念的翻译也体现了诸多局限性,相较于“万日略”,“福音”是一个自明的、被创造的本土性译词,这其实是对语言和概念之间可通约性的内在否定。巴别塔的倒塌隐射出语言自身的局限性,“福音”也许是对“Evangelium”的失真性译介。无怪乎,“宗教史中一半以上不易理解的难题,都是由于以现代语言解释古代语言,以现代思想解释古代思想,因而经常发生误解而产生的,当词语涉及神明时尤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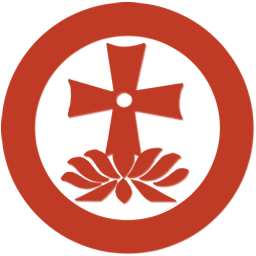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