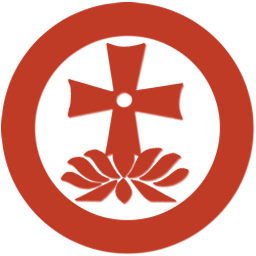摘要: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它与西方基督教在宗教信仰与基本精神上存在着差异。中国道教虽然崇拜多神,但更强调以人为中心,从“我命在我不在天”出发,主张依靠人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得道成 仙”的目标。基督教以对上帝的信仰为中心,从原罪论出发,强调上帝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 意志的体现,以荣耀上帝为人生的使命。因此,在什么是人生幸福的问题上,道教追求保持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注重当下苦难的解脱和现世幸福的获得;基督教宣扬人只有回归到上帝那里,才能重新找回幸 福,故强调人应以信、望、爱为基点,忍受、顺从的现世苦难,追求彼岸世界的永恒幸福。本文通过对中国东晋道士葛洪与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幸福观的比较研究,来呈现道教与基督教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理想所表现出的自觉意识,并力图从一个侧面来展示中西宗教基本精神的差异与互补,以 期为今天的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道教 基督教 幸福观 人与神
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幸福”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 和理解,但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从感觉主义 出发,把幸福看作是在追求满足感官欲望的物质 享受中所得到的快乐,使“所得”大于“所 求”,这是一种不断索取的幸福观,会导致享乐 主义、纵欲主义的盛行;二是从禁欲主义出发, 把幸福理解为通过排斥感官享受而获得超越世俗 生活的精神满足,在“所得”不变的情况下,降 低“所求”,使“所求”小于“所得”,这是一 种自我约束的幸福观;三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把 幸福视为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追求 “所得”与“所求”相平衡。不同的人对幸福的 认识和理解有差异,不同的宗教也有自己独特的 幸福观。二十一世纪以来,“幸福指数”这一概 念已在中国社会中被广泛引用来作为衡量中国民 众生活满意度的一项综合指标,由此可见人们对 幸福的重视。本文通过对中国东晋道士葛洪与罗 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幸福观的比 较研究,来呈现道教与基督教对人的生命存在和 生命理想所表现出的自觉意识,并力图从一个侧 面来展示中西宗教基本精神的差异与互补,以期 为今天的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幸福是人对生活境遇的一种体验与感受、一种 追求与理想。道教从《道德经》的“祸莫大于不 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的思 想出发,认为幸福不在于占有富足的物质生活, 拥有极大的权力名声,而在于保持身体健康和精 神愉悦,故倡导顺应自然、清静自心、知足常乐 地活着,引导人们以一种愉悦平和的心态来对待 生活。道教所谓的幸福是什么呢?一方面,道教有着超越世俗的追求,要摆脱世俗生活对人的种 种束缚,要解决人生的各种痛苦,以使人获得一 种完满的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道教从得道成 仙的基本信仰出发,强调“福莫大于生”!幸福 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拥有多少权力名声, 而在于能够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地活着,永远地 活下去,以至于长生不死。千百年来,道教以 “知足常乐”相号召,把保重身体、快乐地活着 放到了人生幸福的高度,其对生命的热爱形成了 道教幸福观的鲜明特征。 葛洪(283~363)作为东晋时期的著名道 士,他的《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论证了神仙实 有,成仙可能,确立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并 表达了道教的幸福观。葛洪从老子《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的思想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是身体与精神 有机结合而成的,人作为一个有感觉的动物,其 欲望、情感、意志和思想等精神性的因素都受到 身体感受性的影响,身体感受性所遵循的基本原 则就是避免痛苦,趋向快乐。这种利己自爱是人 的天性。人生痛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有身体 以及伴随着身体而产生的种种欲望与苦乐感受。这样,如何减少身体痛苦,如何增加生命的快 乐,就成为道教幸福观的重要内容。
人的身体出世,就意味着个体命运的发生。对于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幸福与不幸的感 觉始终伴随着生命的成长。一个人是否具有生活 的幸福感,生命的愉悦感,往往取决于身体健康 与生命能量的饱满,因此,葛洪选择形体作为长 生成仙之基:“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 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 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 居矣。身(一作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生命是由形体和精神相互配合而成的,形神相合才能使生命焕发出光彩。葛洪虽然主张“形须神 而立”,但更强调“形者神之宅也”,“身(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因而将保持形 体长存作为个体生命超越的先决条件。葛洪看 到,人的生命必须依托于身体而存在,需要满足 身体的各种欲望,没有了身体,就不会有所谓的 心理上的快乐幸福,故将身体作为获得幸福的物 质基础。快乐总是身体的快乐,幸福总是个体生 命的幸福。身体虽与“道”相通,但身体有限而 常有患,而“道”无限而至尊,身体又岂能与 “道”相比?因此超越身体束缚的“得道成仙” 才是生命幸福的终极理想。
而立”,但更强调“形者神之宅也”,“身(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因而将保持形 体长存作为个体生命超越的先决条件。葛洪看 到,人的生命必须依托于身体而存在,需要满足 身体的各种欲望,没有了身体,就不会有所谓的 心理上的快乐幸福,故将身体作为获得幸福的物 质基础。快乐总是身体的快乐,幸福总是个体生 命的幸福。身体虽与“道”相通,但身体有限而 常有患,而“道”无限而至尊,身体又岂能与 “道”相比?因此超越身体束缚的“得道成仙” 才是生命幸福的终极理想。
据此,葛洪一方面提出,人最善者,常欲乐 生,提倡采取种种修道方法来努力保养身体,以 期无限地延长人的生命,因为这是符合“道”的 法则的:“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 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 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这样,神仙 形象中就隐含着希望采用种种技术方法来保全生 命,以使自我能在时间上达到永恒,在空间上消 除任何束缚,永远过着自由自在、恬静愉快生活 的人生理想,但另一方面,葛洪又让人不要执着 于身体,更不能“贪宠有身”。因为人若放纵自 己的欲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好新衣,喜美食, 广宫室,高台榭,积珍宝,这仅是“爱身”,而 非“养生”,最终必然使身与道相违。而那些为 追求财富、名利和声望的人,大部分会倾力“向 外追求”,最终因耗费生命的能量而有损于身心 健康。因此,葛洪认为,由外部的物质利益所引 发愉悦感,往往是暂时的。“夫五声八音,清商 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 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 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 永。”在拥有财富之后,人才会真正体会到,财 富往往并不能带来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的幸福感 和生命的愉悦感。只有恪守着“玄道”,才能达到永远的幸福境界。道教通过对身体的辩证理解,让人将对外在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转向内在养 身,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养身”而又“志欲无 身”,以合于道意。
葛洪认为,仙士与俗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世人犹鲜能甄别,或莫造志行於无名之表,得 精神於陋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 不幸,以荣华为秽汙,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 朝露,蹈炎飙而不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 尘,风驷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行尸之 人,安得见之?”俗人畏死,又不信道,整天钻 营于“邪恶利得”的俗事之中,反而痛苦多多。仙人却懂得俗事、高官、重禄、好衣、美食、珍 宝之味,皆不能致长生。虽然仙人也知道各种俗 事可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满足人的欲望,但 他们为了追求“长生大福”,却专一信道守诫, “不乐恶事”、“不知俗事”、“不贵荣禄财 宝”,才能以愉悦的心情,超越于世俗利益,在 保养身体过程中,获得与道相契的快乐。
仙士与俗人同样是将爱护生命视为幸福观的 重要内容,但对物质利益,道教称之为“俗事” 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幸福观的具体内涵。道 教认为,长生的获得首先需要人消除对俗事的过 分关注:“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 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 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目此得仙寿, 获福在俗人先,卽为身先。”其次,“学仙之 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 无心”,需要人以“少私寡欲”的态度来淡化对 身体的过度保养。“后其身”才能“身先”。这 意味着,仙人在物质享受方面要不与俗人争先, 在物质利益之前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专心于养 身修道,最终才能“获福”在俗人之先,是为 “身先”。道教幸福观以关注人的生命为中心,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幸福观也是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基督教是 “两希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西方文化的 大背景,以至于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始终飘 逸着基督教气息,“使欧洲人开始在‘有信仰的 思想’(或叫‘有思想的信仰’)里展开自己的 历史”。与道教的幸福观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 彩不同,基督教从人对上帝的信仰与崇敬出发, 其幸福观表现出鲜明的神本主义特征。 基督教将上帝奉为宇宙间的唯一真神,是至 高无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 和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支配 者。对人来说,上帝既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人 生得失成败、生死祸福的主宰者;既是人的善恶 行为的审判者,也是人类苦难的拯救者。因此, 什么是幸福?人如何获得幸福?都与人对上帝信 仰相关。如《马太福音》中以耶稣之言的方式提 出的“真福八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 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 安慰。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 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 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 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 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 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 们。”基督教认为,只有这八类人才能得到上帝 恩宠而享受天堂的“真福”。基督教所说的幸福 是与人对上帝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幸福观也是罗马帝国时期重要的基督教思想 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极力论证的神学命题。作为中世纪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在思想成熟后所写的第一部著 作《论真宗教》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只有真正 的宗教才能开辟达致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 基于这样的理念,奥古斯丁认为,人对幸福的渴 望是其自然本性的一种表现,“谁也希望幸福, 谁也希望唯一的真正的幸福,谁也希望来自真理 的快乐。”这种渴望本然地内在于人,这是因为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人对幸福的渴望置于 人的本性中了:“我寻求你天主时,是在寻求幸 福的生命。”然而在实际的生存中,寻求幸福虽 然属于人的本性,但如何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对 象来满足自己的幸福,就成为基督教所说的意志 自由的问题了。 基督教认为,既然一切都是从上帝出发的, 也都是以上帝为最终目的,那么人生也不例外。奥古斯丁曾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他认为, 人的生命由灵魂与肉体有机地结合而成,灵魂是 生命存在之本,生存、存在、理解构成了灵魂的 三一结构。如果说,理解是灵魂的本性,那么, 幸福就是灵魂的存在、生存和理解的共同目标。存在对应于善,生存表现出从大善到小善的移 动,即以痛苦、有限性、无或者非存在的方式来 展现。理解与对上帝信仰相关,它作为存在的一 种方式,是存在和非存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 介或桥梁。奥古斯丁这种基于对灵与肉基础上的 幸福观,与古希腊柏拉图所谓的幸福靠人的理性 能力和现实的德行来实现是有所不同的。在柏拉 图看来,灵魂与肉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立关 系:“灵魂的幸福程度以及对真理(理念)或最 高之神的认识、接近程度,就取决于灵魂在多大 程度上摆脱肉体。在有生之年,人们的灵魂多半 备受肉体的纠缠而远离真理(理念)。”如何使 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接近真理,获得幸福,就成为柏拉图哲学的重要内容。这种“解脱的死亡观”在存在(善)和理解(理性)之间缺少了生存的有限性这一中介环节,导致了对人的自我完 善能力缺乏充分的认识,况且柏拉图哲学中既没 有“罪”的概念,也没有肉体复活的思想。 奥古斯丁对幸福的理解一方面深受柏拉图传 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与灵与肉相关的死亡 的辩证理解开创了基督教神学发展的新方向。奥 古斯丁认为,没有肉体存在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对 上帝信仰的。如果当初人不犯罪,他们的灵与肉 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而永享福乐,但人犯罪了,本 来完好无损的肉体就遭到了损害,尘世的生活带 给人的只是痛苦与不幸。然而,这种以痛苦、有 限、非存在为特征的生存是罪的存在标志,死亡 是对罪的惩罚,也是对肉体的惩罚。这种“惩罚 的死亡观”所包含的宗教性,使基督教的“什么 是真正的幸福”问题突显出来。 基督教认为,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 的,是对那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追求。这一目标 是不可能在世俗生活中达到,因为人生来带有原 罪。“罪就在于无视永恒者而看重可变者。”奥 古斯丁对原罪说的开发,不仅确立了基督教神学 对上帝信仰的理论基础,而且“通过追问罪与责 的来源和根椐而开显出人的另一维更深的超验存 在,这就是自由意志,由此开始了伦理学从‘幸 福生活的指南’向‘罪—责伦理学’的转向”。人的意志是受限制的,世间的任何存在物都是有 限,人间所宣扬的任何善都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 精神满足,更不能确保人内心世界的安宁与平 和。只有上帝才能使人们摆脱自身的烦恼,找到 真正的幸福,因为上帝号召人们应该:安贫、温 良、哀痛、饥渴慕义、慈惠待人、纯洁、和平。只有当人遵循上帝的教导,谨戒情欲、声色、骄 傲、荣华富贵,一心爱那最值得爱的东西—— “首要的善”或“至善”,同时又通过信仰上帝而拥有它时,人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作为最高幸福的“至善”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高于人自己的事物。奥古斯丁说,你想 要幸福,就要寻求高于人自己的事物:“这种幸 福,不要说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 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帝王之位,胜 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第二,它必须是某种永 恒的东西。奥古斯丁把意志转向永恒不变的事 物——上帝。惟有上帝比人的灵魂更高贵,最高 幸福只能在永恒不变的上帝那里找到。“只有能 给予真正幸福的独一的上帝才能赐予这种永恒生 命。”人寻找上帝靠的是意志和爱,不是理智和 认识。相比上帝的存在而言,人的存在就是虚 无,因此,“爱上帝”是人独自无法完成的事 业。人必须通过信仰上帝,依赖上帝的恩典而获 救。“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和恩典论是他本人的生 命经验和保罗书信发生遭遇后的结果。这是他在 自己的生存体验中,在对《圣经》和传统仪式的 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葛洪和奥古斯丁都生活于公元四世纪左右, 葛洪作为魏晋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作 为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不仅奠定了中 世纪道教和基督教的理论基础,而且千百年来对 推动道教和基督教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如果说,理性地思考人的当下存在之局 限,以及建构一种超越世俗而走向神圣彼岸的信 仰是各种宗教教义的核心,那么,宗教最本质的 特征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以及有 限的人对无限的终极神圣的一种永恒的追求。由 此,宗教信仰必然表现出对尚未实现和证实的 “彼岸世界”的确信,并将它作为现实之人的整 个精神活动的一个神圣导向。不同的民族创造了 各具特色的宗教,并力图用一种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来说明自然、社会和人生现象,因此而对人 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近代以 来,道教和基督教都经历了持续改革,在不断扬 弃葛洪和奥古斯丁思想的过程中,它们的教义思 想也在不断发展,但葛洪与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幸 福观,依然在当代的中西宗教文化中有着深远的 影响。从他们的幸福观中可见,以道教为代表的 中国宗教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相比而言, 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则表现出鲜明的神本 主义特征。中西宗教的幸福观之所以各具特色, 主要与它们的信仰特征和基本精神是联系在一起 的。 首先,中西宗教在对神灵的数量、属性和功 能的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基督教中,上帝被 奉为宇宙间的唯一神,耶稣基督、圣灵和上帝是 三位一体的。至高无上,全知、全善、全能、全 在的上帝同时也是人的幸福的源泉:“我寻求你 天主时,是在寻求幸福的生命,我将寻求你,使 我的灵魂生活,因为人的肉体靠灵魂生活,而灵 魂是靠你生活。”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 吗?当然能!但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回归到幸福 之源──上帝那里。对上帝的信仰与对有限之物 的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旨趣,人在生活中所遭遇 的疼痛、苦难和不快乐,都是因为人们远离了上 帝。“为何他们没有幸福?原因是利令智昏,他 们被那些只能给人忧患的事物所控制,对于导致 幸福的事物仅仅保留着轻淡的记忆。”只有当人 们回归到上帝那里,才能重新找回幸福,找到现 实世界所无法提供,而又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幸 福,这种幸福观将基督教以神为本的特征凸显出 来。道教以抽象、神秘的“道”为最高信仰,奉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老子为教祖,又崇拜各路神 灵,是典型的多神教,其中有的神灵是宇宙的造 物主,有的神灵主宰人的吉凶祸福,有的神灵可以帮助消除人的灾难,保佑人的平安。道教众多 的神灵大致可分为三类:尊神、俗神和神仙,它 们大多与人对幸福生活的祈求密切相关。神是出 于天地未分之时的先天真圣,如“三清”、“四 御”、“星君”等;仙是天地开辟之后的得道仙 真者,如“八仙”等。神和仙构成了道教特有崇 拜对象。道教神灵是人类生活的保佑者,也是人 祈求幸福和平安的对象。如道教尊神中的三官大 帝,主管记录人的善恶得失,天官赐福,地官赦 罪,水官解厄,故得到人们的信奉。道教俗神原 是流传于民间的神祗,后被道教纳入自己的神灵 体系,如文昌、门神、财神、灶君、土地、妈 祖、城隍等,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的现实祈 求,为人消灾解难,保佑人平安幸福。例如,财 神主迎祥纳福,下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 使者、利市仙官四神侍奉,专管做生意求发财之 事;门神御凶镇邪,保佑家庭平安;城隍则具有 多种功能,既是“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 也可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佑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还是阴间的神官,主人生死。道教的许多神灵,尤其是一些俗神与人的生活有 密切的关系,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情味和人间气 息,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与基 督教那严厉、独尊、远离人间烟火,却又监视着 人的一举一动的上帝有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表 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 其次,中西宗教对人的看法也有着很大的不 同。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下原 罪,遗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每个人一生下 来就带有原罪。从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性出发,基 督教对人性持有否定的看法。奥古斯丁从人被造 的本体结构,即灵与肉的关系来以说明人的罪性 源于人的各种违背神意、使人堕落的欲望,特别 是人的贪欲:“罪恶并不起源于某种实体,而是 起源于意志中的邪恶”,由此来阐发人对上帝的信仰必要性。人与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人 虽然被称为神的子女,在万物中地位最高,可以 管理和利用万物,但人在“上帝之下,万物之 上”的位置,说明人与神相比,是有罪的、卑微 的、低贱的、必死的。人不仅生来有罪,而且必 然要死:“当最初的人类违反上帝颁布的禁令而 成为不顺从的时,上帝以什么样的死亡来威胁他 们?是灵魂或肉体的死亡,还是整个人的死亡, 或者是被称为第二次死亡的那种死亡?回答是所 有的死亡。”如果说,“第一次死亡”是指整个 人包括灵魂与肉体的死亡,那么,“第二次死 亡”则是灵魂离开上帝却与肉体一起遭受永恒的 惩罚。这样,死亡就不仅是生命的结束,而且也 是上帝意志对人类之罪裁判的结果。据此,罗素 认为:“中世纪教会中许多极其凶恶的事件,都 可追溯到奥古斯丁这种阴暗的普遍罪恶感。”这 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惩 罚的死亡观”既指出了人生痛苦的根源,也使 “复活”成为信仰者一种希望与期待。奥古斯丁 强调,顺应人肉体需要而生活是“自爱”,是以 有限的自身为尺度。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肯定不 是肉体,因为灵魂高于肉体;也不可能是灵魂本 身,因为灵魂不能以自己为尺度。这个尺度只能 来自灵魂之上的上帝,只有上帝才能使灵魂得到 升华。基督教以荣耀上帝、爱上帝为人生的使 命。人若希望得到永恒的幸福,必须以“顺应人 而生活”服从“顺应上帝而生活”。与基督教不同,人是中国道教关注的中心。修道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无限地延长生命,精 神愉悦、身体健康地活着。这与道教对人的本性 的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受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 影响,道教基本上对人性持有肯定的看法。“生 道合一”既是道教所认为的完美人生的具体体 现,也是其人生理想中的最高境界。这样,“贵 生恶死”就成为道教生死观的基本价值取向,由此而肯定了人在宇宙间的较高地位。然而,万事 万物都在经历着一个从生到死的新陈代谢的发展 过程,人也不例外。虽然个体生命只有在超越有 限的羁绊中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但就人脆弱的 生命而言,却始终难以摆脱死亡的威胁。因此, 如何超越有限而走向生命的永恒就构成了道教教 义的基本内涵。葛洪认为,人之所以走向死亡, 乃是自然的原因:“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 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 也,风冷所犯也。”只有“令正气不衰,形神相 卫,莫能伤也”。如果说天道自然,那么,人道 则是自己。每个人寿命的长短,都是因人在后天 的生活中不懂保养造成的。那么,怎样才能最大 限度地让人享尽天年、终其寿命呢?道教宣扬, 如果通过修行而获得了不死之道,那么,就可以 超过这一寿限,得道而成仙。修道的重要性就在 对生命有限的悲剧性认识中凸显了出来。道教虽 然反对追逐外物而掩没人的本真之性,但从养生 出发,又比较关注现世的幸福,把保重身体、快 乐地活着放到了人生幸福的高度,表现出对生命 的热爱。 第三,中西宗教对人与神的关系也有不同的 看法。上帝对人的拯救主要表现为使人的灵魂摆 脱尘世欲望,特别是肉体欲望的束缚,死后进入 天国,获得永生,享有彼岸永恒的幸福,而不是 满足人的对于现世幸福的祈求。这样,在基督教 中,神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神是 人的创造者,人类生活的主宰者,人的善恶行为 的审判者,人的祸福的掌握者;人只能信仰神, 遵从神的旨意,向神祈祷,求神保佑,而决不可 能成为神。在这种神人关系中,神对人具有绝对 的支配权,是人全部生活的中心。人一无所有, 所能做的只是对上帝的祈求和服从。基督教认 为,神的国度建立在天上而不是建立在地上。在今世生活中,人应当清心寡欲、忍受苦难:“我的全部希望在于你至慈极爱之中。把你所命的赐 与我,依你所愿的命令我。你命我们清心寡 欲。……清心寡欲可以收束我们的意马心猿,使 之凝神为一。”由是,传统基督教淡化对世俗生 活幸福的关注,而专注于天国的永福。在神人关 系和人伦关系之间,基督教更看重神人关系,认 为神人关系高于人伦关系,爱上帝的心应超过爱 人的心,爱人也应当是为了上帝而爱人。 道教将“得道成仙”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 标,人与神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道教 诸神可以主宰着人的祸福成败、生死寿夭。人应 当敬畏鬼神,按时祭祀天地鬼神,积德行善,以 求天地鬼神的佑助,获得平安、健康、幸福和长 生不死。而要达到这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的神秘境界,主要依赖于人的自我修炼,修道 “要在守雌抱一,自然返阳生之气,剥阴杀之 形,节气既周,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 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道教把幸福 视为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所谓成仙, 并不是人死后灵魂入仙境,而是指人的长生不 死,人与神仙之间不存在无限的距离与鸿沟。由 此,道教劝导人们返朴归真,过顺应自然、纯朴 真实、恬然淡泊的生活,通过不断炼养身命、存 养本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仙人”,进入生道 合一、天人一体的长生不死之境界,从而使生命 超越有限而获得无限的自由。 最后,中西宗教对人如何解脱生活痛苦而获 得永福有着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基督教从神本主 义出发,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的幸福目 标,宣扬上帝对人的救助与恩典。基督教认为,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世间传播福音,拯救 有罪的世人,并以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人 类赎罪。所以,人的得救本乎上帝的恩典。没有 上帝的恩典,人单单凭藉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摆脱他的罪性进入天堂的。相反,只要神愿意,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也能得到神的赦免,被神拯救, 进入天堂。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派把这一思想推 到极端,提出“因信称义”的“预定论”,认为 能否成为上帝的选民是上帝预先定好的,人的努 力丝毫不能改变上帝的决定,人只能听从上帝的 决定。奥古斯丁在早期比较倾向于认为,人凭借 着理性就具有回到上帝的能力,将恩典看作上帝 的一种邀请,它呼唤人通过理性认识事物的秩 序,并依照世界的秩序来生活,以使灵魂从感觉 的世界中摆脱出来,慢慢地把自身引向最具美德 习惯的完满生活,但随着他人生阅历的增加,他 越加意识到,堕落之后的人是不可能仅靠自身的 理性使自己从罪中摆脱出来。人若要从感觉的世 界中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既要依靠理 性,更需要依靠信仰。因为理性仅是人的灵魂理 解事物之秩序的能力,是有局限的。正如《罗马 书》中说:“我们的得救,赖于希望,并用坚忍 的信心等待你的诺言。”只有把目光转向超感 觉、超经验的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与拯救才能 获得真正的幸福,道教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重现世,倾向 于通过自身的努力修道来追求生命的完满幸福。道教将人的修道视人获得解脱的根本前提,神的 救助只是人的解脱的辅助力量。在道教教义中, 神虽然也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但更是抽 象、神秘的“道”的化身;仙是人通过修炼而成 的,如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中就宣扬,凡 人学道不止而成仙成神:“故奴婢贤者得为善 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 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 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 不止乃与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于北极紫宫中 也,与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得道与成仙 在道教中是一个等价的概念,其根本意旨在于说 明人在修道中的主观能动性及自我拯救的可能性。道教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相反它 认为,现实的痛若人生恰恰是人修道成仙的助 力。因此,修道既要重视精神方面的修炼,也不 可轻视肉体生命的修炼。为此,道教在漫长的历 史中发明了许多修炼方法,如内丹、外丹、服 气、服饵、存思、守一、导引、房中、守庚申 等,希望通过形神俱全、形性双修来无限地延长 人的生命。道教还要求信徒在平常的生活中,不 仅要遵循忠孝仁义等伦理纲常,诵经习符,焚香 礼拜,遵守戒律,而且还要传戒授道,济度众 生,斋醮法事,为人祈福消灾,以积功累德。道 教所宣扬的先修人道,再修仙道,就把得道成仙 的途径置于现实生活之中。 综上所述,道教与基督教的幸福观存在着明 显的差异,在基督教中,上帝是一切的中心与出 发点,人的一切都从属于神,人能否活着、能否 幸福、能否得救都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幸福就 是拥有上帝”,这一方面展现人生的有限性和不 完善性,促使人自觉地意识到自我本有的种种局 限性而杜绝狂妄自大,另一方面,传统基督教以 上帝的绝对神圣性来促进人们追求天国的幸福, 在客观上易忽略人现世生活的质量。道教是从保 持人的生命来看待和设计幸福的。神灵可以对人 的行为进行赏善罚恶,故而是人信仰和崇拜的对 象。神仙则是人修炼而成的,能否成仙取决于人 自身的努力,这一方面可促进人在生命成长的过 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易于使 道教信仰倾向于满足人的现世需要,关注人此世 的平安与幸福。一旦道教信仰过于世俗化,就会 导致宗教生活的神圣性消解及享乐主义流行。中 西宗教在信仰上各具特点,影响了一代代人的精 神世界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了解它们的差异, 可推进中西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研究它们的 互补,则可以更好地来满足今天人们对幸福生活多元化的需要。 而立”,但更强调“形者神之宅也”,“身(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因而将保持形 体长存作为个体生命超越的先决条件。葛洪看 到,人的生命必须依托于身体而存在,需要满足 身体的各种欲望,没有了身体,就不会有所谓的 心理上的快乐幸福,故将身体作为获得幸福的物 质基础。快乐总是身体的快乐,幸福总是个体生 命的幸福。身体虽与“道”相通,但身体有限而 常有患,而“道”无限而至尊,身体又岂能与 “道”相比?因此超越身体束缚的“得道成仙” 才是生命幸福的终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