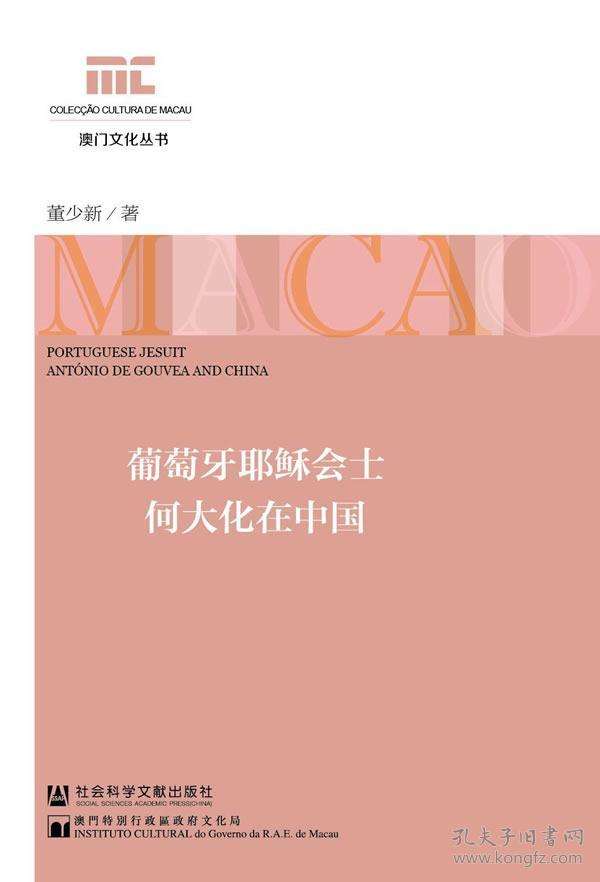
董少新:《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间:2017年12月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东迈
第二章 入华
第三章 武昌
第四章 福州
第五章 历狱
第六章 著述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约于1630年来华,在中国传教47年,足迹达澳门、杭州、上海、武昌、福州、北京、广州等地,创建耶稣会武昌住院(1638-1643),后接替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负责耶稣会福州住院20余年;康熙历狱期间,与其他传教士一同被软禁于广州,期间曾一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副生会长,并参与到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之中;历狱结束后,他于1672年重返福州,五年后去世,葬于福州城外十字山。
何大化在华期间,于西学东渐尤其是西方科学技术传华方面无甚表现,在漫长的中国传教生涯仅写过一部中文教理书《天主圣教蒙引要览》(1655),在以科技传播为导向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何大化这样的传教士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再加上比较而言宫廷传教士比地方传教士更受重视,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耶稣会士比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更受到国内、国际学界的关注,以及学界对葡萄牙文资料使用的局限,何大化长期被学界忽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何大化的在华经历绝非乏善可陈。他编纂过8份耶稣会中国年信(1636,1643-1649),著作有《远方亚洲》(两卷,1644)和《中国分期史》,均为葡萄牙文。所以,何大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更多的是扮演“中学西传”的角色,将大量中国的信息介绍给欧洲。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均未出版过,其影响也远不及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鞑靼战纪》、《中国上古史》、《中国舆图新志》,也不及其同胞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的《大中国志》。但何大化的作品并非全无影响,即使是他的论争对手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s Navarrete, 1618-1686)也承认,其著作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参考了何大化的著作。何大化凭借他的两部著作,奠定了来华耶稣会士史家的地位。
何大化是少数几位完整经历明清鼎革的西方传教士,对在战乱中维系中国天主教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业。就这一点而言,何大化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1637年,来华不久的何大化奉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5-1653)之命前往湖广开教,后因张献忠农民军攻陷武昌,其所建立的湖广传教驻地荒废,他本人则在艾儒略建议下来到福州传教。此时正值满人入关并迅速占领北方诸省,耶稣会于是将中国传教副省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方的耶稣会士以汤若望为代表已开始为清廷效力;而南方则在艾儒略、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何大化、卜弥格(Michael Boym, 1612-1659)、瞿纱微(And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2)等人带领下,与南明政权保持关系。何大化所掌管的福州天主教,受到了隆武朝的重视和礼遇。隆武朝持续时间仅有两年,清军攻占福州后,何大化开始接触满族地方大员,尤其与佟国器等官员关系密切,从而使福建传教区未遭严重破坏,且其立场也由拥护南明抨击满人入侵逐渐转变为寻求满清政府的保护。福州天主教正因为何大化的这一灵活务实的策略,而在明清鼎革之际得以延续。
何大化亲历和见证了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社会,他所留下的宝贵文献,不仅记载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情况,也记录了明末清初中国的社会状况。作为身在中国的西方人,他的观察角度与中国人或许不同,仿佛以第三只眼睛来看待中国发生的一切,比如对于各传教驻地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民风俗的记载,对明清战争的记载,对民间宗教的记载,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补充材料。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将何大化视为早期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之一。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尽量发掘有限的中、西文原始史料,勾勒出何大化在华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尝试考察长期在地方、民间且不以科技为手段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尤其揭示出何大化在明清鼎革之际对天主教在华延续的贡献。本书将何大化在华经历置于明清鼎革的历史背景中,除了传教史之外,亦想表明葡萄牙文档案文献的重要性,以及西文史料对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