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神学年刊2005年26期)
作者:柯毅霖
+++++++++++++++++++++++++++++++++
本文对于福音在中国本地化隐喻的研究,无意也不能钜细无遗地论述这巨大而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所涉及的全部事情及问题。
在此我集中讨论三个题目。在第一章中,我要向大家介绍文化概念及后现代文化、本地化概念及相关的术语以及目前天主教会内对于本地化的讨论。
在第二章中,我要向大家展示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历史过程中的主要节点。然而,本人将迴避以大量篇幅讨论中国礼仪之争问题,因为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献已经十分全面和广泛。
在第三章中,我首先要总括地介绍因文化基督徒的讨论而激发的本地化争论,然后特别介绍刘小枫的神学建议。虽然这讨论不是特别从天主教的角度出发,但它无疑是中国当代基督宗教和神学领域中最有意义的问题之一。本人认为,为此奉上天主教的声音还是值得的。
第一章 本地化在天主教会内的隐喻
何谓文化?
显然,本地化这个概念与文化这个概念是紧密联繫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首先对文化展开描述,那麽本地化就会难于理解。文化不仅不容易定义,而且学者、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之间对这个概念具体应该包括什麽内容也没有形成共识。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与其他罗曼斯语(源自拉丁文的语言)中的相关辞彙很类似,事实上,这个概念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均有相似的历史。然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那些能够代表“文化”的后天习得行为和语义学的一些因素也许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当我们讲“文化人”(a person of culture)的时候,我们是指一个受过教育、对某个学科如艺术、文学、诗歌等有专门而广博知识的人。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精英分子的概念。每个人均通过“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的方式而隶属于某个文化。2这个“文化适应”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它是人们学会在他们所出生和成长的团体中分享和参与生活的过程。文化由一个意义体系组成,在这个体系中,我们所习得的语言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既然人们学习文化,所以教与学的过程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係并不是绝对的,所传授的某些东西可能会失落,而人们总会有新的发现:文化以一种变化的常态而存在。因而,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徵就是它的动力及它的变化模式,基于各种不同的因素,例如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人口和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现等。
习得的模式包括语言、行为,还有符号及其所对应的意义。文化由各种意义体系组成,但它们并不是根本的、普遍的,而是一种共识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人类社会会就不同的关係和意义形成不同的共识。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任何文化是绝对的,所有的文化均是相对的。各种符号的象徵意义必然要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因而保留下来的通常是某种特定的仪式,而其原来的意义已经失落了。
何谓中国文化?
正如前面所提,文化这个术语代表了一个相当複杂多样的概念或现实。文化的複杂性也可以表现为同一文化内的数个次文化的共存,或者同一国家或民族内的多个文化的共存。例如当我们讲中国文化时,我们显得过于概括。何为中国文化?指儒家思想?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民间宗教?风水?传统信仰和实践?毛氏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麽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呢?
而且,中华民族中还有一些次文化,这些“次”文化并不意味着二级文化,而意味着那些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然而这些次文化同样值得人们尊重及拥有尊严。一些次文化包括:少数民族(藏族、彝族、各种依斯兰少数民族等)、又诸如工厂工人、农民、渔人、商人、店主、党员领导、学生等社会团体。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中国具有许多文化,它们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鉴于中国文化的不断变化和多元的特性,本地化的实现显然要比人们的凭空臆想要複杂困难得多。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採用某些中国符号和仪式来表达基督奥迹就能实现本地化。问题远比这要複杂和深远。
后现代和新纪元文化
当代男女所处的后现代环境更增加了定义与描述文化的複杂性,甚至使得定义与描述当代文化也变得十分艰巨。后现代文化是由一系列能够自我生成意义的机构或组织组成,而没有横向和纵向的秩序,谁也不能宣称拥有超越团体的权威。通过大众的沟通与分裂,一些诸如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等複杂现象迫使不同的文化相遇、共存、溷和和重叠。这不仅发生于同一社团内,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体内。许多甚或大多数当代男女同时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而常常採取不同的世界观,这使得世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多元态势。因此,“困惑”这个词便是用来描述生活于地球村中的后现代人。
如上所述,根据定义,文化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转型的状态中,因此文化不仅拥有过去,而且还迈向将来,并且属于将来。那麽所需要的不仅是对某些文化遗产传统展开细緻的研究,而且还是一种想像力练习、一种对于“时代标志”有所关注的意识。本地化的任务必须要考虑这种溷乱和不幸的情形与局面。
后现代性通过它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向基督宗教提出了挑战——这种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不仅关乎事实,也关乎权利。天主的存在或不存在是两个同样无关紧要的选择。
“新纪元”及一些“新宗教”给后现代属于宗教性的回答。它们利用后现代的态度,抛弃深深持守的信仰、思想和传统宗教制度。后现代主义和“新纪元”也分享同样的假设:信仰不如经验重要;信仰的存在基础只是它的实用性。信仰只是偏好取向的问题,而不关乎真理;各种信仰具有同样的、无意义的平等。
不仅在香港,甚至在中国大陆,全球化现象使后现代主义及“新纪元”心态影响更广泛,然而这些思想在香港已然存在。后现代主义及“新纪元”已经透过其激进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融合主义、怀疑主义和分裂主义,加深了世界各地以及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许多当代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分化。许多人也许并没有有意去拥抱后现代主义或“新纪元”本身,但他们却分享它们的一些特征。
何谓本地化?
在过去大约四十年裡,“本地化”已经成为天主教神学讨论和传教实践两个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梵二会议(1962—1965年)、“福音传播”世界主教会议(1974年)及之后的教宗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宗座劝谕(1975年)等教会事件均唤起了人们注意本地化之必要性。自那之后,宗座和教会均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过本地化这个问题,其中包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近的文章:《救主的使命》通谕(Redemptoris Missio, 1990年)、《信仰与理性》通谕(Fides et Ratio, 1998年)和《教会在亚洲》通谕(Ecclesia in Asia, 1999年)。教会文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国际神学委员会于1988年所发表的《信仰与本地化》。除此之外,亚洲主教会议联合会(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已经就此话题发佈了许多文献。
这些有权威的文献将本地化视为启示的一个基本特性,与道成肉身(圣子降生)这奥迹的动力与过程有紧密关系。
天主子的降生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中。在纳匝勒人耶稣身上,天主穿上了典型人性特徵,包括一个人隶属于某个特定民族及某块特定土地。土地的物理特性及其地理限制与圣言取肉身这一事实紧密不分。
因着降生圣言的生活、死亡及从死者中复活,耶稣基督现在已经被宣称为所有造化、全部历史及人类对完善生活之渴望的完成与实现。在他内,所有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纯正价值,如仁慈、翕合主旨、怜悯和正直、非暴力和正义、孝德及与造化寻求和谐等,均寻获了它们的完成与实现。没有任何个人、民族、文化能够对发自人类情境之核心的耶稣的吁求表现得无动于衷。
本地化也被认为与教会的使命紧密联繫在一起。作为教会精髓的福传使命必须要经历一个本地化的过程。如果福音与文化是不同的两种东西,那麽福传与本地化自然就紧密联繫在一起。
天主之国降临于那些深深植根于文化的人们,天国的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借用一些人类文化因素。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相遇过程中,教会不仅要传扬自己的真理与价值、从中为文化添加活力,而且还要採用不同文化中已有的积极因素。这是福传者在宣扬基督信仰、使其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之一部分这一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与各种文化进行融合一直均是教会在世旅程的一部分。
福传与文化相融合的重要后果之一可以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导中显示出来:“教会不能放弃她在与古希腊——拉丁思想进行本地化过程中所获得的东西。放弃这种遗产就是否认天主那在时间与历史过程中引导教会的计画。这个标准对于各个时代的教会来说均是有效的,即使对将来的教会也是如此,她将会以此得知自己因今日和东方文化的交往融合而获益良多。
本地化(Inculturation)及其许多名称
自然,本地化这个术语与文化这个术语一样,也显示出複杂的特性。这种複杂性可以从过去四十年裡人们用于描述这种现实的众多同义词那裡得到很好的展示。一些术语如下:适应化(accommodation)、顺应化(adaptation)、受同化(accultur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或本国化(indigenization)、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文化相关原则(principle of cultural relevancy)、入世化(incarnation)及最近的文化相互关係(inter-culturality)、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文化间对话(cross cultural dialogue)等。每个词均对本地化(inculturation)这个过程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理解。
适应化这个词始自利玛窦(1552—1610年),他用这个词来描述耶稣会的传教方法;众所周知,该方法是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向中国儒家文化宣讲福音。为了能使传教努力更为有效,利玛窦及其同伴们採用了一系列与基督宗教信条没有明显冲突的中国文化特徵(儒家概念、中国成语、寓言故事、历史风范等等)。
顺应化与适应化的意思大致相同:福传者及福音讯息因应对象文化而作出调整与适应。着名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用顺应化这个词来描述利玛窦的方法。8在今天,这对术语(顺应化与适应化)几乎已普遍被弃而不用,儘管它们曾对传教活动的反省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们似乎显示,福音讯息与文化之间的相遇仍很表面。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提出,适应化(或顺应化)应该是迈向本地化的第一步。
本土化或本国化是指教会的地方化(localization),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鉴于梵二会议的努力,它几乎已经普遍完成。索治(Bartolomeo Sorge SJ)等用“文化调和”(cultural mediation)这种说法来描述利玛窦的方法及教宗保禄六世的相关教导。
受同化是人类学家所採用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并没有应用于神学领域。该概念演示了一种经常见于福传过程的现象,便是由文化的接触而引起的动力与变化。
跨文化用于指代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决定因素,或者指某些因素或个人从原来的文化进入另一个不同的文化。在世界的福传史中,无数归信者均经历了后者的过程。当魏若望(John Wetek SJ)对利玛窦的福传方法进行神学反思的时候,他採用了“文化相关原则”的说法。
当入世化一词用于传教领域时,它的意思与本地化(inculturation)非常相近。这个词意味着,福音讯息进入某个特定文化的过程应该模彷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这一过程。
本地化(inculturation)描述的是文化接受福音讯息这一积极过程。该文化的成员理解福音,然后根据福音的存在、行动及传播方式来展现表达福音。12钟鸣旦还指出,福音不仅要通过文化来表达,而且它还要成为“启迪、指引和团结的源泉,对文化进行昇华和重塑,以实现‘新的造化’——这种新造化不仅能够滋养某个具体的文化,而且还能使普世教会受益。”
于1992年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拉辛格枢机提出了“文化相互关係”的说法,这说法更能概括本地化的活力。文化相互关係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事实上基督宗教信仰和福音,并不是一种抽象而孤立的东西,可以从一个文化传送给另一个文化。福音的讯息总是已经切实存在于福传者的文化中。在福传过程中,福音所接触的是两种文化:宣讲者的文化和聆听者的文化。
“文化间神学”表达一种有意识的觉察:福音在某个特定文化中运作,而不会使其绝对化。因此,社会背景在此有很大的重要性。
“处境化”这个词16一直为神学反思所广泛接受,关注的不仅是文化这个(如上面所提过的),难以定义和描述的概念,而且还关注宣讲福音时的特定环境。这特定环境不仅由各种文化因素所组成(未必是一个),而且由社会、经济、政治、种族及其它因素构成。“处境化”这个概念帮助人们在具体情境中作更明确的决定,它允许人们以种族、边际、反潮流和被压迫等群体之一来描述全球化情形。事实上,处境化和本地化(inculturation)这两种说法虽然相关,但它们却描述了不同的概念和行为。
然而,儘管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们为了清晰和简洁的缘故,而倾向于认为“文化相互关係”、“文化间神学”和“处境化”更为恰切,但本人仍沿用“本地化”这词。继续使用这个词的好处因着它现在是正式的教会用语及教会任务这事实得以加强。“本地化”、“文化间神学”和“处境化”被收录于最近的重大作品《传教辞典》中。17由卡尔·穆勒(Karl Muller)18、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哈威.克裡(Harve Carrier)19以及马杰洛.德.斯.阿则维多(Marcello de C. Azevedo)等神学家所作的关于本地化的描述与讨论,基本上与“文化相互关係”、“处境化”和“文化间对话”等所表达的内容一致。
本地化历史
虽然本地化这种说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被正式採用,但这说法所要表达的现实如教会本身一样古老。早在使徒时代,适应化就已经付诸实践。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宗15:1-31)、保禄对外邦人的传教方法以及他在雅典的讲道均是适应化实践的例子。在教会的早期,将各文化与基督宗教信仰进行整合的本地化实践发生在基督信仰与犹太文化、古希腊文化及之后的高卢—日尔曼民族相遇的过程中。早期教会知晓如何将自己插进融入她所遇到的每个文化。完成于西元129年的《致黛奥尼特斯书》(Letter to Diognetus)描述文化与信仰之间的相遇如下:
基督徒与他人的区别,并不在国家、语言或政治制度;他们既不生活在独立的城市裡,也不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言。他们没有特殊的生活方式……然而,儘管他们既生活在希腊城邦中,也生活在夷人城邦之中——这正如他们的命运所决定的——儘管他们也遵守衣食及其它日常习惯,但他们同时也会为他们自己国度的杰出而超凡的制度与机构作出见证。
早期教会神学家们採用了一些诸如“圣言之种”(semina verbi)21和“福音准备”(preparatio evangelica)22等重要神学概念来描述文化与信仰之间的活力关係。
不幸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一些传教力量採用了“白板”(tabula rasa)的方法,意即在宣讲福音之前必须摧毁本土文化。这种受残酷的十字军和西班牙重征服所深深影响的传教方法可以被定义为“反对各国”(contra gentes)的传教,而不是“向各国”(ad gentes)的传教。
然而,宗座从未完全忽略本地化的重要意义。宗座曾多次宣导过这样一种观点:尊重文化及与文化对话是传教活动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在601年,教宗大额我略(国瑞一世)向坎特伯雷的奥斯定发了一封信,该信后来成为讨论本地化的一篇经典文献。
告诉奥斯定,他不应该捣毁各种神庙,而应该捣毁其中的各种偶像。让他先用圣水淨化这些庙宇,然后在那裡搭建祭台及放置圣人的骨髑……当地的人民在看到他们的祭祀之地没有被毁掉之后,可能会更容易消除心中的错误、承认和敬拜真正的神,因为他们来到了他们所熟悉和感觉亲切的地方……他们将不再以向魔鬼奉献的形式来祭献和食用这些祭献品,而是为着荣耀他们称谢为万物之源的天主而祭献。
1658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针对东方的传教团体发佈一个重要的宪章。依照该文献,传教士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语言知识,以当地人民的方言和俚语来履行他们的宣讲职能。不是以武力或以许诺各种好处,而应通过圣言的宣讲和良善行为的模范来使外教人归信。望教者的人格及归信的动机均必须予以调查。领洗前教理讲授必须要坚实牢固,以免新信者将基督之律与外教习俗、真正信仰与偶像崇拜溷合起来。在讲授教理的时候,讲授者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和细心,要儘量少地使用或最好不用体罚。
1659年,传信部向中国的宗座代牧(传教团体的长上)发佈了一份杰出的《指示》,该指示这样说:
只要中国各民族不明显反对宗教和良好习俗,不要尝试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礼仪、习惯和风俗。事实上,有什麽比把法国、西班牙、义大利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输入中国更愚蠢呢?你们所应输入的不是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是信仰。信仰并不会反对、也不会毁坏任何民族的权利和习俗——只要它们并非邪恶,反倒要维护它们。
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针对一些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做法,明令传教士们要尊重他们所工作的民族的各种文化。众所周知,教宗此通谕的初衷是向中国的传教士们作出指示,因为那裡的文化对比格外鲜明。
你们的使命实在神圣,远远高过任何人性层面。主曾对你们每个人教训说:离开你们的人民、你们的土地,动身!你们不必宣扬世间之国,而应宣讲基督之国。
教宗比约十二世在他的首个通谕《至高司祭》(1939年)中重新肯定了本地化的信条:
教会不能也不应想到要轻视或蔑视各民族的特定特徵,这些特徵是人民以一份绝对而明智的自豪所珍视、并视之为宝贵遗产而小心地保存着……那些进入教会的人士,无论他们有什麽样的出身或讲什麽样的语言,他们均必须清楚,他们作为主家裡的孩子均具有平等的权利。
儘管梵二会议上并没有使用本地化这种说法,但却以积极的笔触来描述福音与文化之间的关係:
因为基督之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教会并不会褫夺任何人民的世俗福祉。相反,她会滋养和採用人民的能力、资源和习俗——只要它们是好的。通过採用它们,她会淨化、强化和昇华它们。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中是这样描述本地化这过程:
年轻的教会应该将教会传统因素嫁接到自己的文化上去,从而能够通过相互接触时併发出的活力,强化基督奥体的生命。凡是那些能够用于光荣造物主、来源于他们人民的习俗、传统、智慧、教导、艺术、科学及所有的一切,他们均可借鉴……
对本地化的反对意见
在过去的几十年裡,本地化的概念与实践已经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与反应。为了简洁清晰的缘故,这些反应也许可以概括为下面两种互相反对的态度。
一些保守的天主教徒摒弃梵二的改革,因而仍将本地化视为对他们所认为的教会正确信条和古老传统的一种叛离。依他们看来,本地化是对纯正及正统信仰的背叛,是对当代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精神的致命妥协。我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当中也遇到了这种观点,特别是在成年人和老年人当中。他们只能勉强接受用中文而非拉丁文做的弥撒,并且不满意其他礼仪变化。北京主教座堂救主堂(北堂)内悬挂的一幅油画引起了小小的争议,该画的内容是中华圣母,争议的态度可以约略显示天主教徒对採用中式风格的感受。画中圣母与圣婴耶稣均穿着中国满清宫廷精美刺绣服装。这是一位澳门教会艺术家对教会艺术进行本地化的一种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一次精彩而成功的尝试)。但并不是北京所有的天主教徒能够欣赏童贞玛利亚和圣婴耶稣身上的中国特色。传统的中国教徒认为,耶稣的母亲本身并不是中国人,因而不应该人为地改变为中国人的形象。
大多数中国人对圣母的理解使人们想起了佛教的观音。“我们来自那个世界,我们已经决定离开那种宗教思想倾向,为什麽我们应该再次回归它?”我曾多次注意到,大陆、台湾甚至香港的一些天主教徒反对此种形式的本地化,对传统西方圣像感觉更舒服、更能受到启迪。
激进本地化
对本地化的第二种态度与上面第一种截然相反。一些神学家和牧灵工作者认为,教会的信条构成形式,圣事结构和礼仪传统等均是某个特定文化环境的体现,更具体地讲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表达。甚至耶稣的行为,如用饼和酒作为圣体象徵,也被某些人认为是源自他的文化,因而不具有普世的特性。其结果就是,在他们眼裡,本地化就意味着有多少文化,就可以使用多少文化象徵。耶稣使用了麵饼和葡萄酒,因为他是地中海人,面饼和葡萄酒在那裡是人们最基本、最普遍的食物与饮料。但是现在来自不同文化的基督徒团体应该採用各自的基本的食物,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国家的非洲稷和稷酒。31在中国,依照如此革命性的“本地化”观点看来,最可能的因素将是米饭和茶。在香港,有人说最普遍的午餐要数叉烧饭和普洱茶,它们可以代表本地元素(当然这种建议从未得到官方的认可)。这种激进的建议将会推翻教会悠久的礼仪和信条传统,因而从未实际流行开来,即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梵二之后的喧嚣时期,教会内正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试验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
上面所讨论的两种观点均未能欣赏基督信仰的具体历史特性,也未能意识到文化的複杂和活力特性。然而,关于本地化的争论仍在继续。这讨论在亚洲尤其热烈,因为本地化尝试在这片大陆似乎更为艰巨和具有挑战性。
其中例证之一就是在若望保禄二世于1998年发表《信仰与理性》通谕之后引发的争论。潘彼得(Peter C. Phan)按照阿留索·彼尔斯(Aloysius Pieris)的亚洲神学,欣赏该通谕所表达的观点:基督信仰既能滋养她所相遇的文化,也能被文化所滋养,但是潘彼得也向通谕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特别指出,亚洲的本地化并非通过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讨论而实现,也并非“通过将非基督宗教的礼仪与寺院的习俗纳入基督宗教而实现。相反,本地化的发生是两个群体(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透过在人类团体(并非教会团体)中相遇和日常生活分享而得出的结果。而且,因为亚洲的赤贫和深厚的宗教精神,这些人类团体成员的两个标准就是神秘主义和战斗性。”32梯撒.巴拉苏裡亚(Tissa Balasuriya)发现,“当基督信仰面对古希腊拉丁世界进行本地化的时候,被束缚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上;后来,被缚于西欧的王权之上,结果教会或人类没有因此而受益。教会有关绝对真理、唯一得救途径的主张却联击着历史上最严重违反人权和人类尊严的事实:西欧的殖民主义……以古希腊—拉丁思想表达出来的基督宗教神学偏离了耶稣所宣讲的讯息核心,并且不能容以其他方式表达天主召叫,儘管从实质上讲,所传达的讯息是相同的。”
然而,文化调和总是必要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赤裸的真理,即一种不经过语言和文化介质就能表达的信条。圣经所处的与大多数当代的文化大相迳庭,使得同一圣经很难阅读。鉴于圣经是不变的,为了理解圣经,释经学总是必要的。这个标准也适用于确保信仰大公性和使徒性的教会圣传。基督教条是以确定的信条公式、採用古希腊—拉丁文化中的术语、概念和观点所表达出来。显然,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章 中国的本地化隐喻
唐朝的基督宗教
早期的中国基督宗教是複杂而耐人寻味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发生在西元635年。东方叙利亚教会(根据马丁.帕默【Martin Palmer】的说法“东方礼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们开始了一次意义重大,但为时不久且仍不为人所知的文化交流和本地化的经验。将中国最早基督宗教定义为景教(聂斯多略派)充其量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中国初期传教事业的发源地是波斯教会,该派教会可以追溯到最初期教会。
中亚国家在将基督信仰传入中国的广袤土地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以及基督信仰和佛教之间的互动普遍被人们所忽略。在七世纪之前,波斯帝国越发变得基督化;七世纪后,阿拉伯征服者引入了依斯兰宗教。当时这个国家拥有杰出的基督徒团体和神学流派。635年时,传教扩张到中国,当时唐太宗(627—649年)在国都长安(今西安附近)接见了来自巴格达、由波斯主教阿罗本(Alopen)所带领的使团。
1623年,在陝西省的省会西安附近的周至,人们发现了一块华丽的带有叙利亚文碑铭的碑。1644年,阳玛诺(Manoel Dias the Younger, 1574—1659年)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年)整理发表了带有解释的碑文。艾儒略与中国的知识份子进行了许多对话,他在对话中经常提到西安石碑的伟大发现,称其为中国基督宗教古老临在的具体证据。在十七世纪初期,基督宗教已可以宣称在中国土地上拥有一千年的辉煌历史。
该碑文于781年由波斯僧人写成,记述了阿罗本及其使团抵达中国及之后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故事。碑文的内容向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及许多相关的神学和信条观点。在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在一个完全不同于波斯文化的文化背景中所展开的优秀本地化工作,他们借用了道教与佛教中的术语和概念,如奥体、德性、恩人、隐居、僧侣、住持、寺院、普世救恩、全能者等等。在碑顶有莲花造型,这在佛教中代表“四射光华”。事实上,基督宗教被人们称为“光华四射的宗教”(景教)。在莲花上面是基督宗教的象徵:十字架。
在这短短150年裡所展开的本地化工程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碑文显示了基督宗教、道教和佛教三种宗教传统在神学上有相当程度的糅合。用来描述三位一体的术语是源自道教的代表“三一”的“三有”。佛教经文中的“分身”一词被借来解释基督降生(道成肉身)。
除了西安的石碑,深受佛教思想和术语影响的讲叙利语的传教士和中国归依者们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文献,其中包括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北甘肃敦煌发现的一些文献。这些文献与西安碑文一起,构成了所谓的“中文景教文集”(corpus nestorianum sinicum)——以中文写成的基督宗教文献集,实际上是东方礼教会在中国唐朝扩张的体现。这些文献显示出对当时中国文化有相当的适应。
在第七和第八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会不论在量或是质方面均有增长。虽然698年出现了短暂的迫害,但其后玄宗(712—756年)、肃宗(756—762年)和代宗(762—779年)等皇帝对教会採取支持态度。然而,自841年以后,基督宗教被捲入儒家官员与道家僧侣对日益增长的佛教的斗争之中。对于淼小的基督教会来说,这次迫害是致命性的。
然而,有证据显示,在第一个千年前后的世纪裡,中国教会的一部分在丝绸之路沿路倖存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最不寻常的宗教溷淆(religious contamination)事件发生。印度男性佛教僧人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成为大慈大悲观音,一位在中国最受尊崇的神祗。中国当时的圣母像应该是此转化的唯一影响源泉,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佛教宇宙观中没有女性形象。
元朝的基督宗教
1206年,征服者成吉思汗所统一的蒙古各部落全是基督徒或以基督徒为主,就像成吉思汗的妻子也是基督徒。元朝皇帝忽必烈(1260—1294年),即成吉思汗的孙子,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公主索加塔尼(Sorkaktani)的儿子。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为东方礼教会在中国带来了最后一次复苏。
元朝(1260—1368年)的蒙古统治者对宗教採取一种开放政策,从而使得首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于1294年成功抵达中国。由罗马教宗所派遣、由孟维高(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年)所率领的方济各会士在很多社会上层和宫廷人士中归依为信徒。新约、圣咏和礼仪文献被翻译成蒙古语。方济各会士曾对蒙古族风俗习惯採取了明显的适应措施,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人们的研究。而当民族主义的明朝(1368—1644年)取代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所有外国因素均被禁止。
耶稣会的适应方法
利玛窦及其同伴耶稣会士将基督信仰适应晚明儒家宫廷文化的努力,是中西方历史关係中受到人们研究最多的话题。利玛窦和艾儒略(1582—1649年)及其他耶稣会士以他们仅有的神学工具,启动了一个差点导致中国基督宗教形式的过程,然而这亦要归功于中国归信者最初的贡献。
利玛窦在自己的札记中使用了“适应化”(accommodation)这个词;36他提到,各种团体必须要“按照基督信仰来纠正和适应自己”。37利玛窦此举实际是在模彷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愈显主荣”(ad maiorem Dei Gloriam)这个原则强调了这样一种事实——只有一件事是绝对的,即光荣天主,其他任何事情和这个绝对相比都是相对的。依纳爵将此原则融入耶稣会的生活模式和培育计画中。
因而,我们的会祖曾指示,各处的耶稣会均应讲他们所驻地区的语言:在西班牙,讲西班语;在法国,讲法语;在德国,讲德语;在义大利,讲义大利语,等等;而且,我们的会祖也曾指示,要制定同样的命令,所有地方的耶稣会均应尽力遵守,但要考虑到不同地方和不同人们的性情。
他还清楚地指示,传教过程中要使用同一的方法,诚如该会座右铭所说:“并不是他们要变得像我们一样,而是我们应该要和他们一样。”
利玛窦的前辈们
中国现代的传教故事始自杰出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年)。他在日本所创立的传教事业(1549年)对后来的中国传教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儘管他在日本的三年福传事业的前景十分光明,但沙勿略希望这个国家的归信来得更快一些。沙勿略尝试了一种将对远东传教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传教方法。他强调传教士必须培养知识,为了有效与儒家和佛教徒相处。他还提倡用科技知识陶成的必要性,意在使传教士所传达的讯息更具吸引力。
沙勿略是第一个意识到某种形式的适应对达到预期效果是必要的。沙勿略的经验对后来中国的传教很有用。他注意到,儒家和佛教对社会及文化和个人均有很强烈的影响力。既然儒家和佛教均从中国传入日本,于是沙勿略决定,有必要首先使中国归依,然后日本的归依就水到渠成。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年)是另一个远东伟大耶稣会传教士。他以印度群岛视察员(监会铎,巡阅使)的身份于1574年抵达日本。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实现沙勿略的梦想:适应化方法和开启中国传教事业。既然超过分属不同修会团体的六十多名传教士曾尝试在中国立足而均告失败,于是范礼安对无数的失败尝试进行了反思。和沙勿略一样,范礼安在日本的经验影响了他给中国发出的指示。利玛窦称范礼安为“传教之父”,而钟鸣旦也强调:“没有范礼安,也不会有利玛窦。”
范礼安充分理解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使用翻译的福传是不够的。另外,他还认为,学习口语也是不够的,学写中文和研读中国文学也是必要的。在意识到中国的丰富文化之后,他确信,传教士们必须要研读中国的典籍。他命令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年),也尤其指示利玛窦学习中国的典籍并将其翻译成拉丁文,这样更有利于理解它们并能够在护教和教理工作中引用这些典籍。在他的授意下,罗明坚写出了第一本中文的要理问答,即《天主实录》,于1584年编纂而成。这本书基于在日本已有的一本书再整理而成。不久之后,范礼安命令利玛窦以更多引用中国典籍的方式重写这本要理问答。他还建议,一旦在中国立足之后,传教士们应该穿僧服以突出他们使命中的宗教特性。
范礼安是教会本土化的积极宣导者。与在日本(及在印度)传教士们的普遍趋势形成对比的是,范礼安对地方人士加入圣秩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清楚地看到,教会必须要成为本地的教会,外国传教士绝没有能力独自承担牧灵的重任。
作为首个被允许在中国立足的基督教现代传教士,罗明坚执行了范礼安的新传教政策。他学习中文数年,并与广东省的中国官员成功建立了良好关係。1583年9月,在利玛窦的陪同下,他在广州西边的肇庆永久定居下来。这是中国耶稣会传教事业的起点。罗明坚曾用中文创作58首诗,留下了关于适应精神的着名格言:“我们已经成为中国人,为基督征服中国”(siamo fatti Cini ut Christo Sinas lucrifaciamus)。
利玛窦
一直以来,利玛窦被誉为“最杰出、最聪颖的历史人物之一”、41“中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中间人”、“不朽的人物”。42利玛窦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记忆力惊人,而且是迷人的健谈者及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擅长数学和天文学。利玛窦完成了对《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创立了首个罗马化的文字系统,获得了西方汉学之父的称号。他的灵活性格使他能够吸收大量的中国文化及形成适应化政策,“该政策既是一种大胆的传教战略,也是中欧文化之间相遇的一种精深程式。”
1595年,利玛窦用中文写成第一本书《交友论》。1596年,他重写了罗明坚的要理问答,但直到1663年时才以《天主实义》的名字正式发表,这是中国天主教史中最重要的书籍。1601年,他在北京定居下来,直到他去世。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因为劳累过度而去世,年仅57岁。他壮严肃穆的葬礼及被允许埋在皇家之地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殊待遇,这标志着利玛窦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被接受的程度是极高的。
利玛窦的方法可说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在全球扩张中仅有的几个例外方法之一。利玛窦为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榜样,因为他尝试着为在非基督景环境中形成的礼仪赋予基督的意义,或至少基督的定位。
学者们为利玛窦的适应方法归纳了不同的类型。贝特雷(J. Bettray) 将其整理为六个方面:外在、语言、审美、社会行为、知识和宗教。而根据塞伯斯(J. Sebes)的说法,适应化有四个方面:
生活方式:包括语言、服饰、食物、饮食方式、礼节、出行(如乘学者轿子),等等;
概念的翻译:使用儒家经典及其它中国文化特徵如流行谚语或流行故事、文学典故等表达基督宗教信条的某些层面;
伦理:使用那些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伦理道德因素,如友谊的价值;
礼仪:从某种程度上允许参加儒家礼仪。在利玛窦死后,这个问题成为声名狼籍的中国礼仪之争。
根据哈理斯(G. L. Harris)、德礼贤(P. D'Elia)和古撒尼兹(L. Gutheinz)的说法,利玛窦的适应化传教方法能够通过八重内容框架表达出来:
1. 适应中国人生活方式(包括学说中文和写中文);
2. 结交精英及培养关係网;
3. 担负起确定的社会角色;
4. 将基督宗教宣讲为中国文化中最优秀元素的自然成就;
5. 对天主教信条中何为当信的信条、何为可以改变的东西进行区分;
6. 利用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如科学、艺术和哲学等等;
7. 利用中国社会中沟通交流的管道和技巧;
8. 为本土化教会打下基础。
利玛窦的“剔谬”法
晚明时期的中国传教事业可以为深入而广泛研究任何本地化过程所难免遇到的要求、挑战、困难和挫折提供坚实的基础。晚明时期的中国文化丰富而迥异,利玛窦不得不在这许多可能性之中做出选择。在着僧服、讲佛教语彙十年之后,他毅然转而选择有学问的儒士文化。这个选择正确麽?选择某种文化作为适应化及本地化程式出发点的选取标准是什麽?下面的问题就是适应化和理解正统信条这二者之间的关係。细心的钟鸣旦所提出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显示出对基督信条保持忠诚的问题。让一个归依的中国信徒接受天主为造物主的信条也许并不困难,但他也许不会接受亚当厄娃作为人类始祖的信条,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先皇五帝才具有如此地位,他们才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类始祖。利玛窦并没有就此做出让步,因为在当时:
亚当厄娃是人类原祖的理论是正统教导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接受这个信条;然而今天没有人再强调这一点。但这种正统教导的变化也在其他文化中出现,因为中国的先皇五帝已经不再被中国人视为人类原祖。
利玛窦从所发生的事件和错误中吸取教训,从中国友人那里听取建议,并且不断地系统研习中国文化。利玛窦到达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提前想好对中国的福传方法。他关于所要採取的方式和方法的判断切实随着他在中国工作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利玛窦的态度既忠诚又灵活,利玛窦及其同伴们不仅努力理解和适应中国,而且也被中国所改变。
交友之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利玛窦用中文所写的第一本着作——《交友论》。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概括利玛窦、艾儒略及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方法的核心,那麽这个词就是友谊。他们欣赏并珍视友谊这个典型人文价值。利玛窦及其中国友人从友谊那裡看到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首要而宝贵的共同点:双方对生活均採取一种人文化的方法。事实上,利玛窦是应一个朋友的要求而创作了这篇专论。
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被视为利玛窦计画的宣言:即不通过武力(正如许多人在历史中曾经尝试的)而通过友谊之门进入中国的计画。
利玛窦、艾儒略及其他耶稣会士欣赏友谊这种价值及其在中国人生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友谊是儒家社会思想中所定义的五种关係(五常)之一。在晚明中国,友谊被重新评价为伟大的社会道德。处于明朝衰败时期的十六世纪思想家何心隐(1517—1579年)宣扬友谊是培养团结意识、助人认识到自己对全人类责任。传统的中国人将友谊视为一种自愿的关係,因为关係各方选择了彼此,而并非因为他们被共同的地位或职业而拉到一起。友谊能够促使个人对在家庭及社会阶层中所形成的关係进行补充。
在人文环境中接受教育的耶稣会士发现,中国的学术及文化世界和欧洲的很相似。此次独特的历史相遇的主要共同因素包括:文化人的优越地位、对哲学和科学的热爱、对伦理及实用的讨论胜过教条、基于共同学术兴趣及友谊的社会关係、文化中心诸如城市、学校、学社和协会等的突出地位。中国明朝及欧洲文艺复兴这两个史上最着名的文明通过友谊这个纽带而相遇,这要归功于那些具有人文思想的人们。在儒家的中国,耶稣会士一定感觉和在家裡一样自在放鬆——对他们来说,中国这个世界既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他们的适应化态度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策略,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东西,一种属于人性精神世界的东西。
中国归信者启动了“中国式的基督宗教”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归信者的珍贵贡献还不广为人知,包括在天主教徒中间。明末清初的基督徒学者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体现出双重身份:基督徒兼儒家弟子。被誉为“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也许是最重要的几位拥抱基督信仰、对儒家思想和基督信仰进行活力整合的归依学者,但他们绝不是仅有的几位。另外一组学者基督徒也为中国式的基督宗教做出了贡献:瞿汝夔、冯应京(1551—1610年)、黄明桥(音译Huang Mingqiao)、张赓、李九标、王徵(1671—1644年)、孙元化(1581—1632年)、严莫(音译Yan Mo)、朱宗元(1609—?年)、韩霖(1600—1644年)、吴历(1632—1718年)、张星曜(1633—1715年)尚虎卿(音译Shang Huqing)。
在教会柱石中,杨廷筠最值得被认为是首位华人神学家。作为学者官员,杨廷筠研读儒家经典多年,但他也对非儒家尤其是佛教思想感兴趣。作为1592年的进士,杨廷筠曾身居要职,其中包括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的官职(京兆尹)。他虽然早在1602—1608年间就与利玛窦相识,但直到1613年才领洗入教,即在杭州和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长谈九天之后才决定入教。直到1627年去世,杨廷筠所从事的活动大多与基督信仰有关,显示出极虔诚的信仰生活。在南京教难期间(1616—1617年),他在家里收留保护了数名传教士,创作了八本有关宗教的书,与耶稣会的刊物进行了多次合作(九篇序和跋)。他是艾儒略的好朋友,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结出了果实:艾儒略为杨廷筠编写了传记:《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
杨廷筠具有複杂的生活经历,曾是佛教徒、后来是儒家及基督教徒,这种複杂性进一步加强了其经验及性格的独特价值。杨廷筠对重要信条概念具有清晰的理解,在此我只想提到他对中国的神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两个例子。杨廷筠对三种不同性质的启示展现出聪慧的把握:启示给所有人的“性教”、通过梅瑟的书面启示的“书教”及通过耶稣基督启示的“恩教”。杨廷筠的这套方桉肯定对中国福传问题的正确陈述具有重要意义。杨廷筠也要面对基督的核心角色的问题——基督来自外国,并且对中国古代的圣人来说是陌生的。杨廷筠对基督的独特性有着清楚的神学理解,坚持“恩教”的观点。而且,鉴于“性教”与“恩教”之间有承继性,所以基督的降生与天主在历史中的启示是联繫在一起的,而天主在历史的启示可以回溯到尧、舜、周公和孔子。杨廷筠切实将中华古圣先贤视为“性教”的一部分。性教“被视为正统的传递者,与西方传教士新近所宣扬的完全一样。”早期教会作家和早期教父们对古希腊和拉丁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和圣贤採取了类似的解释方法。
杨廷筠神学的另一个重要而新颖的特徵是天主的概念,他将天主称为“大父母”,一些耶稣会士和归信者沿用了这种说法,尤其是艾儒略。这种说法的渊源取自中国的以阴(雌性因素)阳(雄性因素)概念为基础的宇宙演化学说,这个说法既可用来指述皇帝,又可以指地方官员。
杨廷筠从儒家和基督信仰相互关係这个角度解释了这种说法的意义。根据他的观点,将宇宙视为自己的父母意味着这样一种伦理后果:将世界的所有人类视为自己的亲生兄弟姐妹。而且,这种说法还有另一层意思: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係可以表示天主对人类的关係。同样的关係还能表达天主与人类间令人欣慰的亲密程度。通过这种发展观点,杨廷筠自己也能克服困难去接受天主子降生成人,最初他视此为对天主尊严的贬低,也是对天主的超越性的侵犯。
另外,大父母的说法也有合理的基督论意义:耶稣是大父母与我们人类之间关係的最伟大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自己可以被视为众多兄弟中的首位。长兄的概念和角色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佔据很重要的位置,然而这与西方长兄的概念与角色不同。事实上,它可以是耶稣与中国人亲密关係的有效表达方式,可以帮助中国人感受到,耶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圣经中有数处提到耶稣是长子,尤其是圣保禄的解释:基督是所有受创物的长子,是众多兄弟中的长兄(格1:15;罗8:29)。
这种说法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没有性别倾向的外表。众所周知,当代神学所遇到的最棘手挑战之一就是涵容性语言的问题及将天主与男性权威父权等同起来的问题。圣经中有几处将天主的形象描绘为母亲;对耶稣来说,耶稣呼天主为“父”(阿巴,Abba),这个称呼带有亲密和温柔的意思,并没有任何权威的味道。天主的母亲形象散见于基督宗教灵修史中,只不过这种形象从未成为主流形象。在当代神学中,女权事项是相当重要和敏感的。这个词的广泛使用肯定将有助于较少性别倾向、较少男性化的天主形象的建立。
杨廷筠在归依过程中也遇到了反对的压力。他遇到了佛教徒和儒家反对者的大量批评,超过任何其他华人基督徒。这也显示了他对基督信仰的忠信投入程度。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杨廷筠具有理性和伦理方面的训练和准备以发起福音在中国的本地化这一运动,将自己人民的“禀赋”与福音和谐地整合起来。
礼仪之争
正如本人在序言中所提到的,中国的礼仪之争也许是中国本地化历史中被研究最多的一个话题。此次礼仪之争始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并且持续了150馀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归信基督徒参加某些目的在于尊敬孔子和祖先的礼仪的伦理接受性。这些礼仪是宗教性的或仅仅是民间礼仪?此次争论使耶稣会内部及其与其他修会团体(道明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之间也产生了分歧。在经过数个矛盾的决定、中国派遣至罗马的不同使团及两个赴中国的宗座官方使团之后,宗座最终採用严厉禁令,禁止归依的中国信徒举行此类礼仪。尽管此次争议被教宗本笃十四世于1742年正式结束,但抵达中国的传教士们被命令发誓反对中国礼仪,这种实践一直持续到1939年——当时教宗比约十二世宣布允许进行中国礼仪。
符号论者
这些所谓的符号论者是十八世纪时一些法国耶稣会士,他们提出非常激进及非常有趣的途径将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本地化联繫起来。这些符号论者认为,在中国典籍中,尤其是《易经》中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宗教,而是(我们通过圣经所获得的)原始启示和默西亚预言的真实痕迹。有“国王数学家”之称、被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康熙朝的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便是符号论派的领导人物。其他活跃的符号论者包括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年)和傅圣泽(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年)。鉴于其他耶稣会士及长上的反对,他们的方法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基督宗教艺术在中国本地化的隐喻
罗如望(Joao da Rocha, 1563—1623年)的名字值得我们纪念,因为他于1619年发表了《诵念珠规程》。51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所配的插图,这些插图堪称基督宗教艺术适应中国的首例。在这之前还没有就创立中国基督宗教艺术而进行真正的尝试。
罗如望获取灵感并以之为蓝本的欧洲参考物件是十六、七世纪耶稣会士们所熟知的作品:杰罗姆·内达(Jerome Nadal, 1507—1580年)的《福音故事图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
罗如望请当时杰出画家、艺术理论家董其昌(1555—1636年)或者他的弟子以内达的《福音故事图像》为基础蓝本为他的十五端玫瑰经配木刻插图。
因为他们的高超艺术手法,尤其因为他们的独特理解,罗如望所印製的插图确实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图景显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人物面部表情、外衣、饰物、建筑以及其他建筑因素的刻画(如园林山水和景物)完全是中国特色。
另外,同样的图画结构,但却以中国画的角度重新阐释表达,例如,将图画的内容简化为单一画面。这些插图完全再现了董其昌的风格:在他看来,绘画是对个人内在存有的表达。在其插图中只有基本的主题,在主景周围留下了许多空白空间。这些空白空间并不是为了强调那单一主题的鲜明轮廓,而是神的临在的一种标志。
其中最能体现我们所讲的杰出例子之一是耶稣被钉这一幅。在这幅插图中,中国画家将内达的两幅图画融成一幅,取得了戏剧性的效果。背景中光秃的荒山取代了原画耶路撒冷城的位置,在其衬托之下,孤兀的十字架被突显出来。另外,两个强盗的十字架也被全部略去。耶稣的十字架戏剧性地矗立于天地之间,被无尽的孤寂所包围,似乎只有天主是这一切的目击者。点缀于十字架前后的人群显示出那些虐待和杀死耶稣的士兵们的残忍和无情、那些宣判耶稣的当权者的冷漠,以及妇女们的无助虔敬和悲哀。经此种艺术处理的结果就是一幅具有强烈感情色彩、对主耶稣的受难经过有深厚的中国式理解与阐述的插图。这个有力证据说明,即使在中国传教的早期,中国精神是如何能够吸收及表达耶稣生活及死亡等奥迹。52在罗如望的插图中,基督被赋予中国人的特徵,并且被置于典型的中国环境中。
1637年,在罗如望的《诵念珠规程》发表十七年之后,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53在福州发表,。两年前,艾儒略就发表了八卷本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他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被认为是对前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此书,中国人能够首次使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耶稣的教导,并且能在图画中了解他的主要生活事件。这部作品是一个里程碑使他成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事业中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
当人们比较罗如望和艾儒略的着作时,他们会惊奇地发现,艾儒略并没有如我们所料的那样在此条适应之路上继续前行。艾儒略认为,和欧洲蓝本较近的版本也许会更为合宜,因此他选择忠实地複製内达的原本。然而,艾儒略并没有照搬欧洲蓝本。该书中体现出数处中式风格的重大变化(如“濯足垂训图”),其中最为有趣的莫过于最后一幅“圣母端冕居诸神圣之上”。在该图底端,与宗徒们和其他欧洲人物在一起的是一组欢庆圣母荣耀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物代表有头戴不同头冠的学者、一个士兵及一个留着刘海儿的小孩。在人物和云彩之间是一系列欧式和亚洲式的建筑物(房屋、宫殿及庙宇)。另外一处具有中国特色的细节之处是耶稣右手所持的地球。整幅图切实给人一种印象:欧洲人和中国人一起见证圣母玛利亚被加冕这一重大事件。通过这幅与其他插图截然不同的插图,艾儒略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他们具有和其他成员一样的尊严。
然而,十九世纪对该书的重版故意省去了这幅插图,这切实令人意外。不幸的是,本地化过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传教士的思想和实践变得较为保守,这也许是礼仪之争的许多负面后果之一。
1640年,即艾儒略发表《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三年之后,汤若望代表奥地利皇帝玛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向崇祯皇帝进献一些欧洲宗教贡品,其中包括共有45幅插图的描绘耶稣生平事蹟的图册。同时,汤若望出版了《进呈书像》一册,共包括带有简短解释的48幅插图,55这些插图是进呈给皇帝的插图的复制品。汤若望的插图并不仅仅是对其欧洲图册的照搬複印,而是带有中式改编与适应的重新阐释,尤其是作为装饰元素的脸部表情。56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三部以内达作品为蓝本的画册。汤若望的这本画册之所以变得着名,主要是因为当时反教学者杨光先(1597—1669年)在他的反教文集《不得已》中所摹写的三幅来自汤若望画册中的插图。杨光先撰文指出,这些图画显示,被处以典刑的耶稣是一名罪犯兼谋反之徒。
中国十九世纪的教会艺术几乎均是哥特式风格的翻版,圣母及耶稣圣心的凋像及圣像大多带有十九世纪法国灵修的痕迹。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地化的必要性才再次被纳入各传教团体的议事日程。一些敏锐的传教士如比利时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及诸如宗座代表刚恆毅(Cleso Costatini)的教会领袖大声疾呼,提出模彷欧洲绘画、凋塑和建筑设计的教会艺术不适合中国。作为艺术家的刚恆毅意识到,对中国宗教和艺术思想缺乏敏感的态度是建设真正中国教会的主要障碍。他确信,为了能够更合宜地表达中国人的思想及帮助消除基督宗教是外国宗教这种概念,纯正原创的中国艺术必须要进入中国的教堂。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香港圣神修院的美丽建筑就是在刚恆毅的指示下完成的。它是通过中式风格所获得的良好结果的永久见证。对雷鸣远来说,他巴不得看到教会採取中式艺术,以致于中国的教会能够看到自己的美丽艺术。刚恆毅强烈支持在北京辅仁大学创立教会艺术学院,从此之后,一群前途光明的中国教会艺术家开始通过调和中式风格和基督信仰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才华。
在几十年(1949—1980年)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式教会艺术的事业开始复苏。一些艺术家如何其(He Qi) 、江心(Jiang Xin)、Magdalena Liu、Monica Liu、Paul Zhang等在探讨本地化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促成实现中国式教会艺术。“作为一个中国的教会艺术画家,”何其谈到,“我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完成一项任务,即努力创造中国的教会艺术……我想做一些属于我这个时代的事情。我想起了鲁迅曾说过的话: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开拓者,不应该做人们想要的事情,而应该开拓新的道路。”
在今天的中国,天主教会的许多领袖和信徒对发展一种纯正的本地艺术、一种真正中式艺术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兴趣或不够关心。上面我所提到的一些艺术家感歎,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鼓励和欣赏。然而,通过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教会艺术家们,中国教会艺术是有希望最终成功的。
二十世纪的激烈讨论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裡,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们一直寻求一种能够挽救国家免受耻辱和衰亡的“新文化”。改革者仔细研究了西方的文化、制度和政治模式,将其作为中国所模彷的对象。然而,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与当代西方思想不谋而合,他们确信,当代西方文化达到了顶点,恰恰因为西方摒弃了基督信仰。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的大部分学生均将基督信仰视为进步的障碍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当时的许多知识份子认为,反洋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项主要任务。
因而于1922年爆发的经常将敌视变成公开对抗甚至仇恨的反教运动并不显得十分意外。结果,一些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奋起维护自己的信仰。吴经熊、马相伯、英敛之、陆伯鸿、陆徵祥等一些重要天主教思想家担负起杨廷筠、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所担负起的艰巨任务,即以一种为中国知识份子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达阐释基督信仰。
吴经熊(1899—1986年)也许尤其值得我们一提,因为他曾尝试在东西方之间、儒家人文思想和基督信仰人文思想之间,以及道教修身及基督宗教灵修之间进行一种和谐的整合。在他的着名专论《爱的科学》(1943年作于香港)这本小书中,吴经熊从儒家人文思想和道教修身的角度高超地阐述了圣女小德兰的经验和着述。吴经熊的给人启迪的思想也见于他在《基督人文和中国人文》(Christian Humanism and Chinese Humanism)一书中所做的饶有趣味的研究。
一些诸如刚恆毅和雷鸣远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倡导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地化这项迫切的任务以应付剧烈的挑战。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和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进步及在许多年轻学子中间培养知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建立了无数大学和学校,为妇女提供教育,将西方的医学、科学及其它领域的先进知识带进中国。
关于本地化的争论
本地化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基督宗教之争论中最时常出现也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一。一些中国官员、教会人士及基督宗教研究学者多次指责:基督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并没有在中国繁盛起来,这是因为它未能进行本地化。这些人们通常引用两个例子来支持他们的说法:因为中国礼仪之争,以至未能与儒学进行融合及本地化;与佛教进行对比,据他们说佛教显示了更强大的适应能力,因而能够进入中国的主流。儘管这些说法并不全错,但本人仍持一些反对意见。
1. 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本人认为天主教未能适应帝皇的思想方式,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则将帝皇的理念定义为封建的理念,而不是儒家的理念。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未必就是一种失败。不止一个学者正在就此问题提出不同的评价,其中之一就是台北利氏学社的创始人甘易逢(Yves Raguin),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宗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灵修相遇的研究。我记得一次与甘神父对话,他说如果礼仪之争当初有一个不同的结果,那麽基督宗教恐怕已经成为帝皇儒学理念的一个分支,因而会失去它的定位与身份、它的自由及它的先知性角色。后面我会讨论杨慧林关于基督信仰适应儒家思想这一尝试的批判。
2. 佛教在中国的扩张也被过于简化。佛教徒在中国也时常被迫害及边缘化。即使现在的佛教,至少西藏的喇嘛佛教,也与中国政权不和。总体来讲,佛教缺乏一个中央权力负责监督维护信条,这使它更容易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当利玛窦进入中国开始着僧服的时候(1583年),当时中国的佛教至少有十种派别。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派别(禅宗和淨土宗)就有非常不同的信条与实践。基督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出于自己的本质,一方面瞄准本地化,但另一方面摒弃任何对基本信条内容的嬗变作法。
3. 我从不同意基督宗教在中国彻底失败这说法。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日益增多、自四世纪以来一直将福音讯息作为其生活中心的信徒来说是不公平的。许多信徒从未背弃自己的信仰,哪怕生于一个敌对的环境、面对巨大的反抗和迫害。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政治波澜中,在这段时间裡,作为一个基督徒不亚于犯罪,而且没有任何世俗利益或没有人性保护,他们也在持守着自己的信仰。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信仰比他们的生命更宝贵。他们的见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基督信仰不是外国信仰,基督宗教没有失败。而且,福音在世界内的传播并不是关乎统计数字和世俗成功。有些“基督政权”——大多数人自信是基督徒——也许还不如那些处于少数、没有社会和政治成就和威望的信徒忠实于福音。这些信徒根据真福精神及如芥菜种子一样小的天国精神活出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深度也许超过那些基督徒是大多数、甚至享受宗座外交关係保护的国家的信徒。从福传和神学角度讲,即使一个很小的结果也会具有很大的意义。当人们认真考虑基督宗教在中国曾经及正在面对的困难,人们不禁会惊叹基督徒团体是如何存活四个世纪及如何在今天有如此戏剧性的扩展。
4.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在中国最成功的基督徒团体是那些福音派,他们对本地化没有多大兴趣,只以清晰、简洁和直接的方式宣讲救主耶稣基督的原初教导。尽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传教方法说三道四,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有效地满足了大量寻求灵性意义的人们的需求。
第三章 文化基督徒的中国神学
人文汉语神学
中国大陆特有的文化基督徒现象的出现,在大约过去十年裡唤起了人们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出现新文化契机的希望,或更好说是对于一个本地化的神学的希望。根据中国大陆公认的新教领袖,南京的丁光训主教的说法:“自基督宗教最初以景教的形式传入中国以来,她正在获得中国知识份子前所未有的接受。”
驻扎在伦敦的中国观察家邓守诚同样指出:
本人确信,在近代中国历史中,自利玛窦始,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对基督宗教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1987年时,中国政府将其称为“基督宗教热”。
文化基督徒其实只是由同一批中国学者和中国官员所定义的“基督宗教热”这一更广泛现象的一个独特元素。一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如刘澎的说法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基督宗教热潮。”611993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吴瑛承认“基督文化现象”的存在,“一些学者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承认基督宗教的价值,而且相信这种价值观能够在当代中国形成和发展多元文化过程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这也许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政府研究员口中最早关于“文化基督徒”的描述。
刘小枫(1951—)被认为是文化基督徒的原型,而且也认为是他创造了文化基督徒这个词。在1988至1989年间,刘小枫为大陆月刊《读书》连续撰写了十篇关于二十世纪神学的文章。在其一系列文章的最后,刘小枫提到了文化基督徒这个概念。
自1995年以来,文化基督徒这种说法在大陆内外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一些知识份子拒绝接受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尤其因他们处于基督徒团体之外。批评者指出:一个人要麽是基督徒,要麽不是基督徒;那些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也许是、也许不是基督徒,但文化基督徒是一种滥造的说法。另外一些学者乾脆指出,这种关于“文化基督徒”的讨论根本对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学者无益,因为它只会引起政府的猜疑。
无论如何,本人认为,“文化基督徒”的定义仍能接受,因为这个定义尝试描述一个在中国大学和学术中心确实存在的现象。我想要表达的是,“文化基督徒”这个术语是对一个複杂现象的模煳定义。
在日益壮大的中国大陆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SMCSC,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群中,有些人培养及发展出对基督宗教的个人兴趣,决定对基督宗教课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有些人也许会被基督讯息所吸引,以此成为其个人生活的伦理甚至灵性方向。有些人会将他们称为广义上的“文化基督徒”。定义“文化基督徒”的下一步就是当人从深感兴趣转向接受基督信仰。然而,鉴于这些人在严密监控的学术机构中所处的微妙複杂的地位,或者出于他们个人的种种理由,他们可能不会进入一个教堂而接受洗礼。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基督徒,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一条文化和学术的探索之路而逐渐接受基督信仰。
然而,刘小枫已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在“上帝”的教会裡接受了洗礼。刘小枫喜欢引用魏尔(Simone Weil)的经验作为一个先例:一个人可以是基督徒,但不必具体属于哪个基督徒团体。魏尔(1909—1943年)是着名的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和灵修作家,死于二战期间,年仅34岁。魏尔是一个非常複杂的人:她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神秘主义者及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当魏尔卧病在床时,她拒绝领受食物与药品,为与她饱受纳粹蹂躏的法国同胞保持团结。最后她死了,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她的人民保持了团结。魏尔也拒绝接受洗礼,因为她发现她不同意天主教中的极权因素。将魏尔作为文化基督徒原型的作法诚然有趣。然而,刘小枫还是领了洗,将基督事件变成了他生活的中心。
中国神学和处境化
建设中国神学或汉语神学是文化基督徒现象向神学界(尤其是香港神学界)所提出的最让人兴奋的挑战之一。中国神学计画尤其与刘小枫其人其作联系在一起,直到后来他决定将兴趣转向政治哲学的领域。
按照刘小枫的说法,中国神学不是中国化的神学,即建立于「基督宗教神学这一西方神学必须要适应中国」这观念之上的神学。相反,中国神学是通过使用中国语言世界和经验的形式来表达基督宗教理念神学。如果此举成功,那麽中国神学就会与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语言所构建的神学并肩站在一起,而具有同样的尊严。
刘小枫对中国神学进行了分类:研究存有超越本质的本体论神学(ontological form of theology)和研究存有在时空中的个体——具体——特殊的表现的实体论神学(ontic form of theology)。
第一种形式的神学以现存的思想及其表现形式作为出发点来发展中国神学。具体地讲,儒、道和佛思想是将基督神学重新表达为中国神学的工具与手段。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西方神学家採用柏拉图思想或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过程。
第二种形式的神学强调存在经验及其语言表达。为了能够理解和表达基督事件,这种形式的中国神学採用的是存在——个人——具体——历史及地方层面的语言表达,而不是採用民族思想体系(见第一种形式的神学)。
刘小枫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形式的神学,因为基督事件是对个人的具体存在经验的开放,而不是对民族思想体系开放。基督宗教神学的讨论物件是圣言与个人的具体存在之间的相遇。因而,中国神学是一种本体基督论的神学:基督事件召叫个别存有——他要以具体的语言经验来接受和表达事件中的恩宠。
本人觉得这种说法相当具有启发性及吸引力,儘管刘小枫的本体基督论神学并不仅仅限于中国神学,而属于所有以基督事件为中心召叫个别存有的处境化神学。本人怀疑这种神学是否应该被称为人文汉语神学或基督论汉语神学。此种提议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只是其语言,即中文:刘小枫已经提出了一种母语神学的概念。
这种母语神学将神学家的母语作为表达工具,母语神学的内容是该语言所表达的存在经验以及文化资源。母语神学的读者主要是讲此语言的人。
语言在此已经不是外在的沟通模式,一种工具,而是表达自我现实的具体存在形式,这是海德格(Heiddegger)和维根斯坦(Wittgenstein)的理论。语言不是一种中立的选择,它是人们使自己走向概念存在(conceptual existence)的一种途径与方式。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宿主,是它的形式与界限。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工具,而它本身就是思想。
杨慧林对本地化的批判
杨慧林63断言,中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就好像是欧洲神学家眼中的奥斯维兹和种族灭绝。文化大革命怎麽可能发生呢?它怎麽可能在五千年古老中华文明之后发生呢?两千年的基督化欧洲怎麽也会发生那种事呢?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伦理基础,一种绝对的伦理。在中国传统中,人类与神祗、政治与宗教、行为与规范总会溷在一起,因而伦理判断也许受到世俗利益的扭曲与操控。
这种绝对的伦理只能通过超验的上帝来保证。基督宗教因着它的绝对善(上帝)的标准,与邪恶彻底决裂能使中国的伦理复兴真正受益。
杨慧林强调,基督信仰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为了能做出新的贡献,以及能够向中国文化和社会提出激烈的挑战,基督信仰必须保持它的差异性及新颖性。任何“会通”和“本色化”均会扭曲和稀释基督的讯息。根据杨慧林的说法,即使利玛窦的本地化方法也在适应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基督信仰定位;结果,一些耶稣会士及耶稣会士所启发的文献与着作所呈现的基督信仰与儒家思想非常相似。
何光沪及其来自心的神学
和杨惠林一样,何光沪65也感受到回应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严重道德危机的紧迫性,但他并不悲观。何光沪相信人类精神并且坚信人类宗教精神的普遍性。
按照何光沪的体会,基督宗教不能被归结为“西方的精神”,或者归结为现代化的工具。究其本质,基督宗教包含一种宗教讯息,一种具有灵性、人性和普遍性的讯息。因而他从这一点上不同于杨惠林,他看到了本地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中国和基督宗教之间进行文化对话和宗教对话的益处。何光沪提出的普世宗教精神是以心的概念为中心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核心、重要的圣经概念:人类存有的统一核心,也是人类智慧、意志和感觉的寓所。
也许何光沪的观点有些过于乐观,有点类似于前面所提吴经熊的提议,他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中最佳的成分具有承继性。
在我看来,中国最伟大的财富莫过于儒家的祭天、佛教的修性及道教的贵生。当我们将祭天与偶像崇拜与算命分开来、将修性与遁世厌世分开来、将贵生与迷信实践分开来,那麽我们就离真正的基督宗教不远了。
从这个普世性的角度看,东西方之间的关係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更为积极的态度来看待。
让我们少谈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多谈它们的相互依赖;让我们少谈它们的文化模式,多谈它们共有的宗教精神;让我们少谈它们统一中的区别,多谈它们区别中的统一。
本地化与福音的新颖性
如果我们审视中国的“基督宗教热”的现象,我们会注意到,基督宗教的成功并非因为它对中国文化的适应,而是因为两者的差异。那些在中国最成功的团体是那些大胆宣讲福音讯息、对複杂文化调和没有多少兴趣的团体。这些福音派团体宣讲,“耶稣是你的救主”、并向人们呈现一个热心的信徒团体,去吸引成千上万的新成员。
本人在中国大学和学术机构演讲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了我这种印象。本人在这些学术中心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关于晚明利玛窦、艾儒略及其同伴们所採用的福传方法。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课题,也是本人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内容。我当初认为这个题目能够打动听众,但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演讲的提问阶段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对适应化概念甚至对本地化持批评态度。人们的反对意见可以归纳如下:为什麽当初传教士们要不厌其烦地尝试适应化?他们应该原原本本地呈现基督宗教,然后让人们自己决定接受与否。即使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们也提出了类似问题。这些学生和学者担心,适应化过程会使基督精神和纯正基督信条黯然失色。
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引起中国学生和学者们对适应化和本地化进行猜疑的因素。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坚持,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必须要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本地化显然是一种合理而必要的神学进程,但政府所提倡的适应化就是一种对宗教自治领域的不合理干预。
当然,本地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前面提过的,为文化下定义这难题一样,人们必须採取审慎的态度,无须热衷于在本地化过程中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根据本人的经验与理解,中国大陆的学人之所以受到基督宗教的吸引,并不是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而是因为它的迥异,尤其是耶稣的人格,更是引发人们的兴趣与沉迷的重要因素。他的人性、生活方式、价值观、他的言行、他的与边际人群为伍、他的苦难与受辱、他的无辜等等,这些都是耶稣身上吸引中国学者的关键。
本地化是一项神学、传教和牧灵的根本任务。然而经验显示,没有任何人曾因本地化而归向基督,而是因为与基督有一份以个人作为存有的接触,即在刘小枫反思中处于非常重要地位基督工程的救赎。换言之,这种对于本地化的关注是合理而必要的,但它不应该取代耶稣的福音教导。基督奥迹的核心是基督的十字架,而十字架是不能“本地化”的。没有十字架的屈辱(Scandal),福音将会失去它的内在能量与威力。
福传必须要保留耶稣基督的“神学”独特性,应该忠实于逾越节羔羊原初教导、忠实于“多样性”、忠实于十字架上的屈辱与愚蠢。基督信仰不能被呈现为对人类问题及需要的简单宗教回答,如在新纪元和新宗教中所实践的那样。在大约过去三十年裡,尤其是在天主教会内部,本地化和宗教间对话一直被人们视为对亚洲传教的挑战。本人想要指出的是,耶稣的人格,基督论问题,最近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传教挑战,在亚洲尤为如此——因为亚洲在文化上对宗教多元化、本地化和宗教间对话格外敏感。
需要天主教会的更多参予
本人相信,“基督宗教热”、文化基督徒、构建中国神学及本地化教会的任务等是天主教神学界所面对的重大挑战。本人希望,中国教会中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加入到构建中国神学的努力中。另外,如果中国大陆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们错过与伟大天主教神学传统和当代天主教神学成果相遇的机会,那麽将会令人非常遗憾。本人希望,一个天主教高等学府能够接受这个挑战。这裡面有更多人们加入的空间,尤其是中国的神学教师们。
本人坚信,一个本地化的基督宗教需要更深厚的灵修与教会经验。个人浸沉入基督的奥迹中是一个新神学的诞生所必须的。伟大的神学家均是属灵之人。相反,当使用的手段仅限于学术和理性方面时,本地化也不可能实现。一些本地化的实验如果不是投入深厚的信仰,可能只会获得有限的成果。本人还坚信,那些接受此圣神奇恩与先知能力的人将会带来神学的革新。那种通过文化方式而真诚怡人地表达出来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从上而来的恩典以及一种极待完成的使命。这些东西不是大家围在桌子旁就能讨论得出的。
本人还真心希望,教会与研究基督宗教学者及文化基督徒们的更多合作和对话,将会有助于对中国大陆的基督宗教做出一个更为平衡和开放的评价。对整体的基督宗教,特别是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形成一种少为意识形态式的、少为偏见的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成就。如果这一切真能实现,那麽社会、公众意见及政府官员对基督宗教信仰就会持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基督宗教在中国最终将会享受更多自由、享受更好待遇,这些均是完成本地化任务的先决条件。
结语:北京的两个墓地
2001年10月1日,本人到北京参加利玛窦进京400周年纪念(1601年)的活动。与会的人们被邀参观北京的两个“教会墓地”。此次参观带来的是一份惊喜:这两处墓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了过去教会传教士们的临在。
第一处墓地是北京西北、位于北京行政学院(前党校)的栅栏墓地。栅栏墓地环境清幽,为苍松翠柏及挺拔黄杨所环抱。此处墓地拥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最早的教会墓地。该处收藏有义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的三通墓碑,他们生前为中西之间带来了互惠的交流。其馀六十馀通墓碑纪念了其他中外杰出的传教士们。
1997年,耶稣会神父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 于1999年去世)与北京行政学院的研究员高智瑜、余三乐和林华一起整理出版了一本纪念栅栏墓地历史的精美图书,收录了全部墓碑的图片。该书名为《虽逝犹存》,颇能唤起人的思古情怀。
第二处墓地远没有栅栏出名。事实上,它并不是一处独立的墓地,而是来自正福寺的三十六通天主教传教士的墓碑。1710年时,法国耶稣会士曾在正福寺开闢墓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处墓地被完全拆毁。北京文物局设法保存了这三十六通墓碑。今天,位于京西美丽的五塔寺(梵文真觉,中文五塔寺)内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存着这些墓碑。博物馆四周景色宜人,视野开阔。在这裡,人们可以看到古老的印度式佛塔、无数民间宗教和道教象徵、许多和儒家及中国典籍相关的题字与诗词。在这个彙集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的地方,来访者会看到一处专门开闢出来,用以纪念清代的教会传教事业临在的地方。
基督宗教象徵与中国传统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和儒家的主题与象徵放置在一起。这似乎是一种见证、一种标志:基督宗教确实是中国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一部分。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结果在某些人眼裡似乎那样的微不足道,以致于被他们认为是一种失败。结果诚然淼小和具争议性,但却打下了良好和耐久的基础。
这些“教会”墓地在今天的北京是一个清晰的标志、一种有力的见证:从福传的角度看,即使微小的结果也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教会墓碑似乎也是一种先知性的符号、一种希望的标志、一个所有中国及世界宗教均应遵循的指路标:这是一条尊重、对话、相互理解和欣赏之路、一条合作与团结之路。在中国及在其他任何地方,宗教、文化和艺术均应该致力于促进人类精神、促进人类愿望,并以各种形式和方式促进人类尊严。从这个角度讲,基督宗教肯定有些重要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中国:中国不能没有基督宗教,而基督宗教也不能没有中国。
这两处墓地,或在古刹佛塔的掩映之下,或在苍松翠柏的衬托之中,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人士引人遐思的墓碑的环抱中,为到访者提供了一种美妙独特的氛围,使之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地化的隐喻进行深刻而有创造性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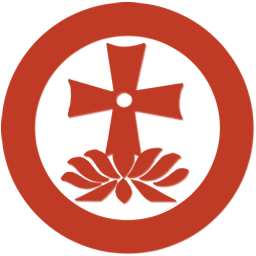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