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下,中国计量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单位,以及新的计量仪器。它们的出现,扩大了传统计量的范围,为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些新的计量分支一开始就与国际相接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计量开始了向近代计量的转化。
关键词:明末清初,传教士,计量
中图分类号:NO92:TB9.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3)03-0000-00
明末清初,中国传统计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计量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单位,以及新的计量仪器,它们扩大了传统计量的范围,为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些新的计量分支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计量开始了向近代计量的转化。这一转化,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促成的。
一、角度计量的奠基
中国传统计量中没有角度计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可用于计量的角度概念。
像世界上别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不接触到角度问题。但中国人处理角度问题时采用的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办法,他们没有发展出一套抽象的角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统一的角度体系(例如像西方广泛采用的360°圆心角分度体系那样),以之解决各类角度问题。没有统一的体系,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单位,当然也就不存在相应的计量。所以,古代中国只有角度测量,不存在角度计量。
在进行角度测量时,中国古人通常是就其所论问题规定出一套特定的角度体系,就此体系进行测量。例如,在解决方位问题时,古人一般情况下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地支来表示12个地平方位,如图1所示。在要求更细致一些的情况下,古人采用的是在十二地支之外
又加上了十干中的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和八卦中的乾、坤、艮、巽,以之组成二十四个特定名称,用以表示方位。如图2所示。但是,不管是十二地支方位表示法,还是二十四支方位表示法,它们的每一个特定名称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区域之内没有进一步的细分。所以,用这种方法表示的角度是不连续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只具有特定用途的角度体系,只能用于表示地平方位,不能任意用到其他需要进行角度测量的场合。因此,由这种体系不能发展出角度计量来。
在一些工程制作所需的技术规范中,古人则采用规定特定的角的办法。例如《考工记·车人之事》中就规定了这样一套特定的角度:
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欘,一欘有半谓之柯,一柯有半谓之磬折。
矩是直角,因此这套角度如果用现行360°分度体系表示,则
一矩 = 90°
一宣 = 90°× 1/2 = 45°
一欘 = 45°+ 45°× 1/2 = 67°30′
一柯 = 67°30′+ 67°30′×1/2= 101°15′
一磬折 = 101°15′+ 101°15′× 1/2 = 151°52′30″
显然,这套角度体系只能用于《考工记》所规定的制车工艺之中,其他场合是无法使用的。即使在《考工记》中,超出这套体系之外的角度,古人也不得不另做规定,例如《考工记·磬氏为磬》条在涉及磬的两条上边的折角大小时,就专门规定说:“倨句一矩有半。”即该角度的大小为:90°+ 90°×1/2= 135°。这种遇到具体角度就需要对之做出专门规定的做法,显然发展不成角度计量,因为它不符合计量对统一性的要求。
在古代中国,与现行360°分度体系最为接近的是古人在进行天文观测时,所采用的分天体圆周为365 1/4度的分度体系。这种分度体系的产生,是由于古人在进行天文观测时发现,太阳每365 1/4日在恒星背景上绕天球一周,这启发他们想到,若分天周为365 1/4度,则太阳每天在天球背景上运行一度,据此可以很方便地确定一年四季太阳的空间方位。古人把这种分度方法应用到天文仪器上,运用比例对应测量思想测定天体的空间方位,[1]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定量化了的天文观测资料。
但是,这种分度体系同样不能导致角度计量的诞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古人当成角度。例如,西汉扬雄就曾运用周三径一的公式去处理沿圆周和直径的度之间的关系[2],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3] 。
非但如此,古人在除天文之外的其他角度测定场合一般也不使用这一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古人的天文观测结果时,尽管可以直接把他们的记录视同角度,但由这种分度体系本身,却是不可能演变出角度计量来的。
传教士带来的角度概念,打破了这种局面,为角度计量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发挥了很大作用。
利玛窦为了能够顺利地在华进行传教活动,采取了一套以科技开路的办法,通过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示自己所掌握的科技知识,博取中国人的好感。他在展示这些知识的同时,还和一些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了一批科学书籍,传播了令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一新的西方古典科学。在这些书籍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一书。《几何原本》是西方数学经典,其作者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Euckid,约前325-约前270)。该书是公认的公理化著作的代表,它从一些必要的定义、公设、公理出发,以演绎推理的方法,把已有的古希腊几何知识组合成了一个严密的数学体系。《几何原本》所运用的证明方法,一直到17世纪末,都被人们奉为科学证明的典范。利玛窦来华时,将这样一部科学名著携带到了中国,并由他口述,徐光启笔译,将该书的前六卷介绍给了中国的知识界。
就计量史而言,《几何原本》对中国角度计量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它给出了角的一般定义,描述了角的分类及各种情况、角的表示方法,以及如何对角与角进行比较。这对于角度概念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普适的角度概念,角度计量就无从谈起。
除了在《几何原本》中对角度概念做出规定之外,利玛窦还把360°圆心角分度体系介绍给了中国。这对于中国的角度计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计量的基础就在于单位制的统一,而360°圆心角分度体系就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统一的可用于计量的角度单位制。正因为这样,这种分度体系被介绍进来以后,其优点很快就被中国人认识到了,例如,《明史·天文志一》就曾指出,利玛窦介绍的分度体系,“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以之布算制器,甚便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分度体系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了中国人进行角度测量的单位基础。就这样,通过《几何原本》的介绍,我们有了角的定义及对角与角之间的大小进行比较的方法;通过利玛窦的传播,我们接受了360°圆心角分度体系,从而有了表示角度大小的单位划分:有了比较就能进行测量,有了统一的单位制度,这种测量就能发展成为计量。因此,从这个时候起,在中国进行角度计量已经有了其基本的前提条件,而且,这种前提条件一开始就与国际通用的角度体系接了轨,这是中国的角度计量得以诞生的基础。当然,要建立真正的角度计量,还必须建立相应的角度基准(如检定角度块)和测量仪器,但无论如何,没有统一的单位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角度计量,因此,我们说,《几何原本》的引入,为中国角度计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角度概念的进步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地平方位表示方面,自从科学的角度概念在中国建立之后,传统的方位表示法就有了质的飞跃,清初的《灵台仪象志》就记载了一种新的32向地平方位表示法:“地水球周围亦分三百六十度,以东西为经,以南北为纬,与天球不异。泛海陆行者,悉依指南针之向盘。盖此有定理、有定法,并有定器。定器者即指南针盘,所谓地平经仪。其盘分向三十有二,如正南北东西,乃四正向也;如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乃四角向也。又有在正与角之中各三向,各相距十一度十五分,共为地平四分之一也。”[4]这种表示法如图3所示。由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表示地平方位时,已经采用了360°的分度体系,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人们还放弃了那种用专名表示特定方位的传统做法,代之以建立在360°分度体系基础之上的指向表示法。传统的区域表示法不具备连续量度功能,因为任何一个专名都固定表示某一特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任何一处都属于该名称。这使得其测量精度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它不允许对区域内部做进一步的角度划分。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变区位为指向,以便各指向之间能做进一步的精细划分。这种新的32向表示法就具备这种功能,它的相邻指向之间,是可以做进一步细分的,因此它能够满足连续量度的要求。新的指向表示法既能满足计量实践日益提高的对测量精度的要求,又采用了新的分度体系,它的出现,为角度计量的普遍应用准备了条件。
角度概念的进步在天文学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受传教士影响所制作的天文仪器,在涉及到角度的测量时,毫无例外都采用了360°角度划分体系,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时,介绍了欧洲的天文仪器,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徐光启就曾经专门向崇祯皇帝上书,请求准许制造一批新型的天文仪器。他所要求制造的仪器,都是西式的。徐光启之后,中国人李天经和传教士罗雅各(Jacques Rho,1590-1638)、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以及后来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也制造了不少西式天文仪器,这些仪器在明末以及清代的天文观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西式天文仪器,无疑“要兼顾中国的天文学传统和文化特点。比如,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在仪器上刻画了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这样的标记,用汉字标数字。”[5]但是,在仪器的刻度划分方面,则放弃了传统的365 1/4分度体系,而是采用了“凡仪上诸圈,因以显诸曜之行者,必分为三百六十平度”的做法[6]。之所以如此,从技术角度来看,自然是因为欧洲人编制历法,采用的是60进位制,分圆周为360°,若在新仪器上继续采用中国传统分度,势必造成换算的繁复,而且划分起来也不方便。所以,这种做法是明智之举。
随着角度概念的出现及360°分度体系的普及,各种测角仪器也随之涌现。只要看一下清初天文著作《灵台仪象志》中对各种测角仪器的描述,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总之,360°分度体系虽然是希腊古典几何学的内容,并非近代科学的产物,但它的传入及得到广泛应用,为中国近代角度计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温度计的引入
温度计量是物理计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近代的温度计量的基础是在清代奠定的,其标志是温度计的引入。
温度计量有两大要素,一是温度计的发明,一是温标的建立。在我国,这两大要素都是借助于西学的传入而得以实现的。
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有关温度问题的思考。气温变化作用于外界事物,会引起相应的物态变化,因此,通过对特定的物态变化的观察,可以感知外界温度的变化。温度计就是依据这一原理而被发明出来的。中国古人也曾经沿这条道路探索过,《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中就有过这样的说法:
“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
这里所讲的,通过观察瓶里的水结冰与否,就知道外边的气温是否变低了,其实质就是通过观察水的物态变化来粗略地判定外界温度变化范围。《吕氏春秋》所言,当然有其一定道理,因为在外界大气压相对稳定情况下,水的相变温度也是相对恒定的。但盛有水的瓶子绝对不能等同于温度计,因为它对温度变化范围的估计非常有限,而且除了能够判定一个温度临界点(冰点)以外,也没有丝毫的定量化在内。
在我国,具有定量形式的温度计出现于十七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介绍进来的。南怀仁是比利时人,1656年奉派来华,1658年抵澳门,1660年到北京,为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当助手,治天文历法。这里所说的温度计,就是他在其著作《灵台仪器图》和《验气图说》中首先介绍的。这两部著作,前者完成于1664年,后者发表于1671年,两者均被南怀仁纳入其纂著的《新制灵台仪象志》中,前者成为该书的附图,后者则成为正文的一部分,即其第四卷的《验气说》。关于南怀仁介绍的温度计,王冰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7]
南怀仁的温度计是有缺陷的:该温度计管子的一端是开口的,与外界大气相通,这使得其测量结果会受到外界大气压变化的影响。他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受亚里士多德“大自然厌恶真空”这一学说影响的结果。考虑到早在1643年,托里拆利(E. Torricelli,1608-1647)和维维安尼(V. Viviani,1622-1703)已经提出了科学的大气压概念,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此时南怀仁还没有来华,他应该对这一科学进展有所知晓。可他在20多年之后,在解释其温度计工作原理时,采用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这种做法,未免给后人留下了一丝遗憾。而且,他的温度计的温标划分是任意的,没有固定点,因此它不能给出被大家公认的温度值,只能测出温度的相对变化。这种情况与温度计量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在西方,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于1593年发明了空气温度计。他的温度计的测温结果同样会受到大气压变化的影响,而且其标度也同样是任意的,不具备普遍性。伽利略之后,有许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从事温度计的改善工作,他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订能为大家接受的温标,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就曾为缺乏一个绝对的测温标准而感到苦恼,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也曾为温度计的标准化而做过努力,但是直到1714年,德国科学家华伦海特(Gabriel Daniel Fahrenheit,1686-1736)才发明了至今仍为人们所熟悉的水银温度计,[8]10年后,他又扩展了他的温标,提出了今天还在一些国家中使用的华氏温标。又过了近20年,1742年,瑞典科学家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1701-1744)发明了把水的冰点作为100°,沸点作为0°的温标,第二年他把这二者颠倒了过来,成了与现在所用形式相同的百分温标。1948年,在得到广泛赞同的情况下,人们决定将其称作摄氏温标。这种温标沿用至今,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温标。
通过对比温度计在欧洲的这段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南怀仁制作的温度计存在着测温结果会受大气压变化影响的缺陷,尽管他的温度计的标度还不够科学,但他遇到的这些问题,他同时代的那些西方科学家也同样没有解决。他把温度计引入中国,使温度计成为人们关注的科学仪器之一,这本身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温度计量领域所具有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南怀仁之后,我国民间自制温度计的也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清初的黄履庄就曾发明过一种“验冷热器”,可以测量气温和体温。清代中叶杭州人黄超、黄履父女也曾自制过“寒暑表”。由于原始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对于这些民间发明的具体情况,还无从加以解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活动,表现了中国人对温度计量的热忱。
南怀仁把温度计介绍给中国,不但引发了民间自制温度计的活动,还启发了传教士不断把新的温度计带到中国。“在南怀仁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李俊贤、宋君荣、钱德明等,他们带到中国的温度计就比南怀仁介绍的先进多了。[9]” 正是在中外双方的努力之下,不断得到改良的温度计也不断地传入了中国。最终,水银温度计和摄氏温标的传入,使得温度测量在中国有了统一的单位划分,有了方便实用的测温工具。这些因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温度计量的萌生,而近代温度计量的正式出现,则要到20世纪,其标志是国际计量委员会对复现性好、最接近热力学温度的“1927年国际实用温标”的采用。在中国,这一步的完全实现,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了。
三、时间计量的进步
相对于温度计量而言,时间计量对于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更为重要。中国的时间计量,也有一个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开始的标志,主要表现在计时单位的更新和统一、计时仪器的改进和普及上。
就计时单位而言,除去年月(朔望月)日这样的大时段单位决定于自然界一些特定的周期现象以外,小于日的时间单位一般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中国人对于日以下的时间单位划分,传统上采用了两个体系,一个是十二时制,一个是百刻制。十二时制是把一个昼夜平均分为12个时段,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地支来表示,每个特定的名称表示一个特定的时段。百刻制则是把一个昼夜平均分为100刻,以此来表示生活中的精细时段划分。
十二时制和百刻制虽然分属两个体系,但它们表示的对象却是统一的,都是一个昼夜。十二时制时段较长,虽然唐代以后每个时段又被分为时初和时正两部分,但其单位仍嫌过大,不能满足精密计时的需要。百刻制虽然分划较细,体现了古代计时制度向精密化方向的发展,但在日与刻之间缺乏合适的中间单位,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正因为如此,这两种制度就难以彼此取代,只好同时并存,互相补充。在实用中,古人用百刻制来补充十二时制,而用十二时制来提携百刻制。
既然十二时制与百刻制并存,二者之间就存在一个配合问题。可是100不是12的整数倍,配合起来颇有难度,为此,古人在刻下面又分出了小刻,1刻等于6小刻,这样每个时辰包括8刻2小刻,时初时正分别包括4刻1小刻。这种方法虽然使得百刻制和十二时制得到了勉强的配合,但它也造成了时间单位划分繁难、刻与小刻之间单位大小不一致的问题,增加了相应仪器制作的难度,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它与时间计量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传教士介绍进来的时间制度,改变了这种局面。明朝末年,传教士进入我国之后,在其传入的科学知识中,首当其冲就有新的时间单位。这种新的时间单位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的“刻”的改造上,传教士取消了分一日为100刻的做法,而代之以96刻制,以使其与十二时制相合。对百刻制加以改革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例如汉哀帝时和王莽时,就曾分别行用过120刻制,而南北朝时,南朝梁武帝也先后推行过96刻制和108刻制,但由于受到天人感应等非科学因素的影响,这些改革都持续时间很短。到了明末清初,历史上曾存在过的那些反对时刻制度改革的因素已经大为削弱,这使得中国天文学界很快就认识到了传教士的改革所具有的优越性,承认利玛窦等“命日为九十六刻,使每时得八刻无奇零,以之布算制器,甚便也。”[10]
传教士之所以首先在角度计量和时间单位上进行改革,是有原因的。他们要藉科学技术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首先其天文历法要准确,这就需要他们运用西方天文学知识对中国的观测数据进行比较、推算,如果在角度和时间这些基本单位上采用中国传统制度,他们的运算将变得十分繁难。
传教士对计时制度进行改革,首先提出96刻制,而不是西方的时、分、秒(HMS)计时单位体系,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兼顾。在西方的HMS计时单位体系中,刻并不是一个独立单位,传教士之所以要引入它,自然是因为百刻制在中国计时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行用已久,为了适应中国人对时间单位的感觉,不得不如此。传教士引入的96刻制,每刻长短与原来百刻制的一刻仅差36秒,人们在生活习惯上很难感觉到二者的差别,接受起来也就容易些。由于西方的时与中国十二时制中的小时大小一样,所以,新的时刻制度的引入,既不至于与传统时刻制度有太大的差别而被中国人拒绝,又不会破坏HMS制的完整。所以,这种改革对于他们进一步推行HMS制,也是有利的。
96刻制虽然兼顾到了中国传统,但也仍然遭到了非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康熙初年杨光先引发的排教案中,这一条被作为给传教士定罪的依据之一。《清圣祖实录》卷十四《康熙四年三月壬寅》是这样记录该案件的:“历法深微,难以区别。但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为九十六刻,……俱大不合。”不过,这种非议毕竟不是从科学角度出发的,它没有影响到天文学界对新法的采纳。对此,南怀仁在《历法不得已辨·辨昼夜一百刻之分》中的一段的话可资证明:“据《授时历》分派百刻之法,谓每时有八刻,又各有一奇零之数。由粗入细,以递推之,必将为此奇零而推之无穷尽矣。况迩来畴人子弟,亦自知百刻烦琐之不适用也。其推算交食,求时差分,仍用九十六刻为法。”南怀仁说的符合实际,自传教士引入新的时刻制度后,96刻制就取代了百刻制。十二时制和96刻制并行,是清朝官方计时制度的特点。
但新的时刻制度并非完美无暇,例如它仍然坚持用汉字的特定名称而不是数字表示具体时间,这不利于对时间进行数学推演。不过,传教士并没有止步不前,除了96刻制之外,他们也引入了HMS制。我们知道,HMS制是建立在360°圆心角分度体系基础之上的,既然360°圆心角分度体系被中国人接受了,HMS这种新的计时单位制也同样会被中国人接受,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开始推行96刻制的时候,一开始推行的就是“周日十二时,时八刻,刻十五分,分六十秒”之制,[11]这实际上就是HMS制。这一点,在天文学上表现最为充分,天文仪器的制造首先就采用了新的时刻制度。在清代天文仪器的时圈上,除仍用十二辰外,都刻有HMS分度。[12]这里不妨给出一个具体例子,在南怀仁主持督造的新天文仪器中,有一部叫赤道仪,在这台仪器的“赤道内之规面并上侧面刻有二十四小时,以初、正两字别之,每小时均分四刻,二十四小时共九十六刻,规面每一刻平分三长方形,每一方平分五分,一刻共十五分,每一分以对角线之比例又十二细分,则一刻共一百八十细分,每一分则当五秒。[13]” 通过这些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在这台新式仪器上,采用的就是HMS制。前节介绍温度计量,南怀仁在介绍其温度计用法时,曾提到“使之各摩上球甲至刻之一二分(一分即六十秒,定分秒之法有本论,大约以脉一至,可当一秒)”[14] 。这里所说的分、秒,就是HMS制里的单位。这段话是HMS制应用于天文领域之外的例子。
在康熙“御制”的《数理精蕴》下编卷一《度量权衡》中,HMS制作为一种时刻制度,是被正式记载了的:
历法则曰宫(三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秒(六十微)、微(六十纤)、纤(六十忽)、忽(六十芒)、芒(六十尘)、尘;
又有日(十二时,又为二十四小时)、时(八刻,又以小时为四刻)、刻(十五分)、分,以下与前同。 [15]
引文中括号内文字为原书所加之注。引文的前半部分讲的是60进位制的角度单位,是传教士引入的结果;后半部分就是新的时刻制度,本质上与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时刻制度完全相同。《数理精蕴》因为有其“御制”身份,它的记述,标志着新的时刻制度完全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有了新的时刻制度,没有与时代相应的计时仪器,时间计量也没法发展。
中国传统计时仪器有日晷、漏刻、以及与天文仪器结合在一起的机械计时器,后者如唐代一行的水运浑象、北宋苏颂的水运仪象台等。日晷是太阳钟,使用者通过观测太阳在其上的投影和方位来计时。在阴雨天和晚上无法使用,这使其使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在古代,日晷更重要的用途不在于计时,而在于为其它计时器提供标准,作校准之用。漏刻是水钟,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均匀水流导致的水位变化来显示时间。漏刻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时仪器,由于古人的高度重视,漏刻在古代中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其计时精度曾达到过令人惊异的地步。在东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漏刻的日误差,常保持在1分钟之内,有些甚至只有20秒左右。[16] 但是,漏刻也存在规模庞大、技术要求高、管理复杂等缺陷,不同的漏刻,由不同的人管理,其计时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显然,它无法适应时间计量在准确度和统一化方面的要求。
与天文仪器结合在一起的机械计时器也存在不利于时间计量发展的因素。中国古代此类机械计时器曾发展到非常辉煌的地步,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就规模之庞大、设计之巧妙、报时系统之完善等方面,可谓举世无双。但古人设计此类计时器的原意,并非着眼于公众计时之用,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演示仪器,向君王等表演天文学原理,这就注定了由它无法发展成时间计量。从计量的社会化属性要求来看,在不同的此类仪器之间,也很难做到计时结果的准确统一。所以,要实现时间计量的基本要求,机械计时器必须与天文仪器分离,而且还要把传统的以水或流沙的力量为动力改变为以重锤、发条之类的力量为动力,这样才能敲开近代钟表的大门,为时间计量的进步准备好基本的条件。在我国,这一进程也是借助于传教士引入的机械钟表而得以逐步完成的。
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来的是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17]罗明坚是意大利耶稣会士,1581年来华,先在澳门学汉语,后移居广东肇庆。他进入广东后,送给当时的广东总督陈瑞一架做工精制的大自鸣钟,这使陈瑞很高兴,于是便允许他在广东居住、传教。
罗明坚送给陈瑞的自鸣钟,为适应中国人的习惯,在显示系统上做了些调整,例如他把欧洲机械钟时针一日转两圈的24小时制改为一日转一圈的12时制,并把显示盘上的罗马数字也改成了用汉字表示的十二地支名称。他的这一更改实质上并不影响后来传教士对时刻制度所做的改革,也正因为这样,他所开创的这种十二时辰显示盘从此一直延续到清末。
罗明坚的做法启发了相继来华的传教士,晚于罗明坚一年来华的利玛窦也带来了西洋钟表。当还在广东肇庆时,利玛窦就将随身携带的钟表、世界地图以及三棱镜等物品向中国人展示,引起中国人极大的好奇心。当他抵达北京,向朝廷进献这些物品时,更博得了朝廷的喜欢。万历皇帝将西洋钟置于身边,还向人展示,并允许利玛窦等人在京居住、传教。
明朝灭亡之后,来华传教士转而投靠清王朝,以继续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在他们向清王朝进献的各种物品中,机械钟表仍然占据突出地位。汤若望就曾送给顺治皇帝一架“天球自鸣钟”。在北京时与汤若望交谊甚深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精通机械学,他不但为顺治帝、康熙帝管理钟表等,而且自己也曾向康熙帝献钟表一架。南怀仁还把新式机械钟表的图形描绘在其《灵台仪象志》中,以使其流传更为广泛。在此后接踵而至的传教士中,携带机械钟表来华的大有人在。还有不少传教士,专门以机械钟表师的身份在华工作。
传教士引进的机械钟,使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兴趣。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主持历局时,在给皇帝的奏请制造天文仪器的清单中,就有“候时钟三” [18],表明他已经关注到了机械钟表的作用。迨至清朝,皇宫贵族对西洋自鸣钟的兴趣有增无减,康熙时在宫中设有 “兼自鸣钟执守侍首领一人。专司近御随侍赏用银两,并验钟鸣时刻”。在敬事房下还设有钟表作坊,名曰“做钟处”,置“侍监首领一人”,负责钟表修造事宜。[19]在上层社会的影响之下,制作钟表的热情也普及到了民间,大致与宫中做钟的同时,在广州、苏州、南京、宁波、福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家庭作坊式的钟表制造或修理业,出现了一批精通钟表制造的中国工匠。清廷“做钟处”里的工匠,除了一部分由传教士充任的西洋工匠之外,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钟表制作的普及,为中国时间计量的普及准备了良好的技术条件。
中国人不但掌握了钟表制作技术,而且还对之加以记载,从结构上和理论上对之进行探讨和改进。明末西洋钟表刚进入中国不久,王徵在其《新制诸器图说》(成书于1627年)中就描绘了用重锤驱动的自鸣钟的示意图,并结合中国机械钟报时传统将其报时装置改成敲钟、击鼓和司辰木偶。清初刘献廷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则详细记载了民间制钟者张硕忱、吉坦然制造自鸣钟的情形。《四库全书》收录的清代著作《皇朝礼器图式》中,专门绘制了清宫制作的自鸣钟、时辰表等机械钟表的图式。嘉庆十四年(1809),徐光启的后裔徐朝俊撰写了《钟表图说》一书,系统总结了有关制造技术和理论。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机械钟的工艺大全,亦是当时难得的一部测时仪器和应用力学著作。[20]
中国的钟表业在传教士影响之下向前发展的同时,西方钟表制作技术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欧洲中世纪的机械钟计时的准确性并不高,但到了17世纪,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他和惠更斯各自独立地对摆的等时性和摆线做了深入研究,从而为近代钟表的产生和兴起也为近代时间计量奠定了理论基础。1658年,惠更斯发明了摆钟,[21]1680年,伦敦的钟表制造师克莱门特(Clement)把节摆锚即擒纵器引入了钟表制作。[22]这些进展,标志着近代钟表事业的诞生。
那么,近代钟表技术的进展,随着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是否也被及时介绍进来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说,明亡(1644)之前,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钟是欧洲古代水钟、沙漏,中世纪重锤驱动的钟或稍加改进的产品;从清顺治十五年(1658)起,传入中国的钟表有可能是惠更斯型钟;而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就有可能主要是带擒纵器和发条(或游丝)的钟(表)。”[23]即是说,中国钟表技术的发展与世界上近代钟表技术的进步几乎是同步的。这为中国迈入时间计量的近代化准备了基本条件。当然,只是有了统一的计时单位、有了达到一定精确度的钟表,没有全国统一的计时、没有时间频率的量值传递,还不能说时间计量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的要求。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地球观念的影响
中国近代计量的萌生,不仅仅是由于温度计和近代机械钟表等计量仪器的出现,更重要的,还在于新思想的引入。没有与近代计量相适应的科学观念,近代计量也无从产生。这些观念不一定全部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但没有它们,就没有近代计量。上述角度观念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地球观念也同样如此。
地球观念的产生,与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无关,但它却是近代计量产生的前提。如果没有地球观念,法国议会就不可能于18世纪90年代决定以通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长度的基本单位,从而拉开近代计量史上米制的帷幕。没有地球观念,也就不可能有时区划分的概念,时间计量也无从发展。所以,地球观念对于近代计量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地球观念。要产生科学的地球观念,首先要认识到水是地的一部分,水面是弯曲的,是地面的一部分。中国人从来都认为水面是平的,“水平”观念深入到人们思想的深层,这无疑会阻碍地球观念的产生。在中国古代几家有代表性的宇宙结构学说中,不管是宣夜说,还是有了完整理论结构的盖天说,乃至后来占统治地位的浑天说,从来都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地球观念。到了元朝,西方的地球说传入我国,阿拉伯学者扎马鲁丁在中国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其中一台叫“苦来亦阿儿子”,《元史·天文志》介绍这台仪器说:
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毬,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这无疑是个地球仪,它所体现的,是不折不扣的地球观念。但这件事“并未在元代天文学史上产生什么影响”。[24]到了明代,地球观念依然没有在中国学者心目中扎下根来。这种局面,要一直到明末清初,传教士把科学的地球观念引入我国,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地球观念的引入,从利玛窦那里有了根本改观。《明史·天文志一》详细介绍利玛窦引进的地球说的内容:
其言地圆也,曰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隐。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
这是真正的地球说。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接受地球学说,首先是接受了西方学者对地球说的论证,所谓“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就是地球说的直接证据。对这一证据,唐代一行在组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时就已经发现,但未能将其与地球说联系起来。而传教士在引入地球说时,首先把这一条作为地球说的证据进行介绍,从而引发了中国人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他们承认了地球说的正确性。对此,有明末学者方以智的话为证,他在其《通雅》卷十一《天文·历测》中说:“直行北方二百五十里,北极出高一度,足征地形果圆。”
中国人接受地圆说,当然就承认水是地的一部分。方以智对此有明确认识,他在《物理小识》卷一《历类》中说:“地体实圆,在天之中。……相传地浮水上,天包水外,谬矣。地形如胡桃肉,凸山凹海。”方以智的学生揭暄更是明确指出了水面的弯曲现象:“地形圆,水附于地者亦当圆。凡江湖以及盆盎之水,无不中高,特人不觉耳。”[25]这样的论证,表明西方的地球说确实在其中国支持者那里找到了知音。
有了地球观念之后,计量上的进步也就随之而来。例如,在计量史上很重要的时差观念即是如此。时差观念与传统的地平大地说是不相容的,所以,当元初耶律楚材通过观测实践发现时差现象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得出科学的时差概念。事情起源于一次月食观测。根据当时通行的历法《大明历》的推算,该次月食应发生在子夜前后,而耶律楚材在塔什干城观察的结果,“未尽初更而月已蚀矣。”他经过思考,认为这不是历法推算错误,而是由于地理位置差异造成的。当发生月食时,各地是同时看到的,但在时间表示上则因地而异,《大明历》的推算对应的是中原地区,而不是西域。他说:
盖《大明》之子正,中国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西域之初更也。西域之初更未尽时,焉知不为中国之子正乎?隔几万里之远,仅逾一时,复何疑哉!
但耶律楚材只是提出了在地面上东西相距较远的两地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时间表示,可这种时间表示上的差别与大地形状、与两地之间的距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则语焉不详。不从科学的地球观念出发,他也无法把这件事讲清除。而不了解这中间的定量关系,时间计量是无法进行的。
地球观念的传入,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利玛窦介绍的地球说明确提到,“两地经度相去三十度,则时刻差一辰。若相距一百八十度,则昼夜相反焉。”[26]这是科学的时区划分概念。有了这种概念,再有了HMS时制以及达到一定精度的计时器(如摆钟),就为近代意义上的时间计量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地球观念的传入,还导致了另一在计量史上值得一提的事情的发生。这就是清代康熙年间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工作。这次测绘与中国历史上以前诸多测绘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首先在全国范围进行了经纬度测量,选择了比较重要的经纬度点641处,[27]并以通过北京钦天监观象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以赤道为零纬度线,测量和推算出了这些点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实测了全国地图,使经纬度测量成果充分发挥了其在地图测绘过程中的控制作用。显然,没有地球观念,就不会有这种测量方法,清初的地图测绘工作,也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成就。这种测绘方法的诞生,是中国传统测绘术向近代测绘术转化的具体体现。
地球观念还与长度基准的制订有关。国际上通行的米制,最初就是以地球子午线长度为基准制订的。传教士在把地球观念引入中国时,也隐约认识到了地球本身可以为人们提供不变的长度基准。在《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八十五卷所载之《新法历书·浑天仪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设圈有大小,每圈俱分为三百六十度,则凡数等而圈之大小、度之广狭因之。乃地亦依此为则。故地上依大圈行,则凡度相应之里数等。依小圈亦有广狭,如距赤道四十度平行圈下之里数较赤道正下之里数必少,若距六十七十等之平行圈尤少。则求地周里数若干,以大圈为准,而左右小圈惟以距中远近推相当之比例焉。里之长短,各国所用虽异,其实终同。西国有十五里一度者,有十七里半又二十二里又六十里者。古谓五百里应一度,波斯国算十六里,……至大明则约二百五十里为一度,周地总得九万余里。乃量里有定则,古今所同。
所谓大圈,指地球上的赤道圈及子午圈,小圈则指除赤道圈外的所有的纬度圈。这段话告诉我们,地球上的赤道圈及子午圈提供了确定的地球周长,各国在表示经线一度的弧长时,所用的具体数值虽然不同,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长度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以地球的“大圈”周长为依据制订尺度基准,那么这种基准是最稳定的,不会因人因地而异。
《新法历书》的思想虽未被中国人用来制订长度基准,但它所说的“凡度相应之里数等”的思想在清代的这次地图测绘中被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用活了,玄烨据此提出了依据地球纬度变化推算距离以测绘地图的设想。他曾“喻大学士等曰”:
天上度数,俱与地之宽大吻合。以周时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时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 [28]
细读康熙的原话,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天上度数”,实际是指地球上的纬度变化,他主张在测绘地图时,要通过测量地球上的纬度变化,按比例推算出(而不是实际测量出)相应地点的地理距离。因为纬度的测量比地理距离的实测要容易得多,所以康熙的主张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富有科学道理的。他的这一主张,是在地球观念的影响之下提出来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康熙时的地图测绘,有不少书籍都从计量的角度,对测绘用尺的基准问题做过探讨,例如,《中国测绘史》就曾提出:在测绘全国地图之前,“爱新觉罗·玄烨规定,纬度一度经线弧长折地长为200里,每里为1800尺,尺长标准为经线弧长的0.01秒,称此尺为工部营造尺(合今0.317米)。
玄烨规定的取经线弧长的0.01秒为标准尺度之长,并用于全国测量,乃世界之创举。比法国国民议会1792年规定以通过巴黎的子午圈全长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1米(公尺)标准长度及其使用要早88年和120多年,(1830年后才为国际上使用)。”[29]因此,这一规定显然是中国近代计量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
《中国测绘史》的这种观点富有代表性,涉及于此的科学史著作几乎众口一词,都持类似看法。空穴来风,这种看法应当有其依据,因为康熙本人明确提到“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这里天上一度,反映的实际是地上的度数,因此,完全可以按照地球经线弧长来定义尺度。
但是,如果清政府确实按康熙的规定,取经线弧长的0.01秒为标准尺度之长,则1尺应合现在的30.9厘米(按清代数据,地球周长为72 000里,合129 600 000尺,取其四千万分之一为1米,则得此结果),但清代营造尺的标准长度是32厘米,[30]二者并不一致。可见,认为清代的营造尺尺长是按照地球经线弧长的0.01秒为标准确定的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是不一致的。
再者,如果康熙的确是按地球经线弧长的0.01秒作为营造尺一尺的标准长度,那也应该是首先测定地球经线的弧长,然后再根据实测结果确定尺度基准,制造出标准器来,向全国推广,而不是首先确定尺长,再以之为基准去测量地球经线长度。
此外,文献记载也告诉我们,康熙朝在统一度量衡时,是按照“累黍定律”的传统方法确定尺长标准的,与地球经线无关。在康熙“御制”的《数理精蕴》中,就明确提到:
里法则三百六十步计一百八十丈为一里。古称在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今尺验之,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盖古尺得今尺之十分之八,实缘纵黍横黍之分也。 [31]
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与所谓“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相符的“今尺”尺长基准,是按照传统的累黍定律的方法确定的。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以地球经线弧长为标准确定尺度基准的影子。
显然,康熙并未设想要以地球经线弧长为准则确定尺度,更没有按这种设想去制订国家标准器,去推广这种标准。他在测量前指示人们按照“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的比例测绘地图,是为了测量的简便,与长度基准的确定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1]关增建. 中国古代物理思想探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224~232.
[2]扬雄. 难盖天八事〔A〕.隋书·天文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关增建. 传统365 1/4分度不是角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5).
[4]南怀仁. 灵台仪象志〔A〕.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九十一卷·灵台仪象志三〔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影印本.
[5]张柏春. 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60.
[6]新法历书·浑天仪说一〔A〕. 历法大典〔Z〕. 第八十五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7]王冰. 南怀仁介绍的温度计和湿度计试析〔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6,(1).
[8](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 周昌忠,等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04-108.
[9]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265.
[10]明史·天文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嘉庆会典》卷六十四〔Z〕.清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王立兴. 计时制度考〔C〕.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C〕. 第四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41.
[13]南怀仁. 新制六仪〔A〕. 新制灵台仪象志〔M〕.卷一.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14]南怀仁. 新制灵台仪象志. 卷四. 验气说〔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15]御制数理精蕴〔A〕. 四库全书〔Z〕. 文渊阁.
[16]华同旭. 中国漏刻〔M〕. 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1.
[17]曹增友.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57.
[18]明史·天文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19]清史稿·职官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0]戴念祖.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05.
[21]〔日〕汤浅光朝. 科学文化史年表〔M〕. 张利华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54.
[22](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 周昌忠,等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28.
[23]戴念祖. 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99.
[2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 中国天文学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201.
[25]方以智. 地类·水圆〔A〕. 物理小识〔M〕. 卷二. 万有文库本.
[26]明史·天文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27]《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测绘史〔M〕. 第二卷.北京:测绘出版社,1995. 119.
[28]康熙五十年四月至六月〔A〕. 清圣祖实录〔Z〕卷二四六.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9]《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测绘史〔M〕. 第二卷.北京:测绘出版社,1995. 111.
[30]丘光明、邱隆、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23.
[31]度量权衡〔A〕御制数理精蕴〔Z〕. 下编卷一. 四库全书〔Z〕. 文渊阁. 关于康熙用“累黍定律”方法确定度量衡基准的过程,亦可参见《律吕正义》、《律吕正义后编》等书。
The Missionarie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Metrology
GUAN Zengjian
(Department for the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
Abstract:During 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science carried by missionaries, some new concepts and units as well as metrological apparatus entered the field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trology. Those new things broadened the r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trology and layed a foundation for the birth of some new metrological branches in China. Those new branches were coincide with that in Europe. Their appearance means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trology began its transition stage to modern metrologies.
Key Words:the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M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ies, missionaris, metrologies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上海 200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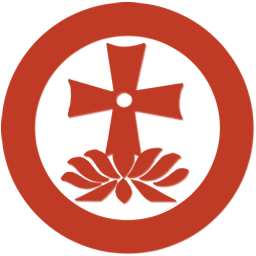









评论